《罪孽的报应》:如何叫醒装睡之人
2025-09-18
作者:
来源:
大众日报
 【 查看PDF版】
【 查看PDF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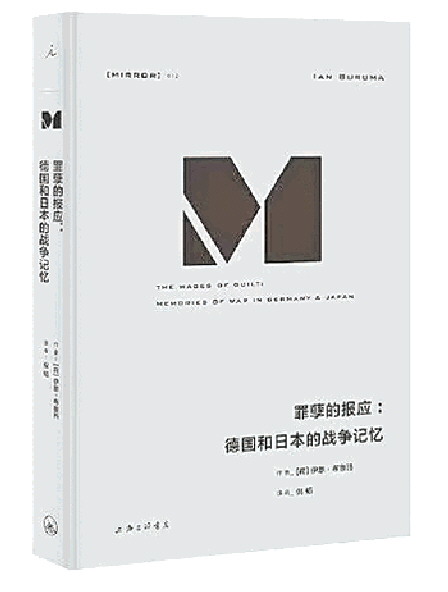 |
|
|
 |
|
东京审判现场
|
□ 本报记者 卢昱
本报实习生 董诗妮
1931年9月18日晚,日军自编自导炸毁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嫁祸于中国军队,突然袭击并侵占了沈阳城和东北30多座城市。这一天成为日本大规模武装侵华的开始,也是法西斯国家正式发动侵略之日。自此以后,直到1945年,中国大地惨遭侵略,暴行让无数生灵失去了生命。
如今,94年过去了。同样是二战侵略国、战败国,皆背负着沉重的历史罪责,战后德国和日本“应对”各自战时罪孽方式却不同:一个是以悔罪的方式承受责任;另一个则是以抵赖和健忘来躲避报应。
为何德国能“觉醒”,日本却始终“装睡”?荷兰作家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的《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一书,正围绕这一话题展开。它不是一本传统的历史著作,而是一部“政治游记”——作者穿梭于柏林与东京,广岛与奥斯威辛,教科书编辑部与战争纪念馆之间,用对话、观察、文化符号与集体记忆的碎片,拼出了一幅关于“罪与罚”的图景。
根源是“不负责任的体制”
布鲁玛想知道的不仅仅是历史本身,还有历史如何被记忆、被扭曲、被利用。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他走遍德国与日本,访谈学者、教师、政治家、老兵、艺术家,甚至右翼分子。他参加广岛和平纪念仪式,也参观柏林犹太博物馆;他听家永三郎讲述教科书诉讼三十年,也听保守派议员辩解“南京大屠杀是夸大”;他关注德日两国关于反思战争的书籍、戏剧、电影、电视节目。
最终,布鲁玛得出结论:德国与日本的差异,不是文化性的,而是政治性的。不是“罪文化”与“耻文化”的区别,而是宪政体制、教育理念、政治精英与公共讨论空间的差异。他拒绝用“文化差异”来简单解释一切,也没有步《菊与刀》作者本尼迪克特的旧路,不认为德国人天生有“罪感”、日本人天生有“耻感”。他指出:真正决定一个国家如何面对过去的,不是民族性,而是政治结构。
德国战后经历了政治制度的彻底重构,纳粹被彻底清算,宪法爱国主义取代了民族主义。尽管“竭力遗忘”与“无法哀悼”的心理也曾一度困扰德国人,但他们最终选择正视历史,用异常残酷的方式面对自己的记忆,“德国人的记忆就像一条巨大的舌头,一遍遍地舔舐,想要找出那颗隐隐作痛的坏牙”——不惮于留存,并且在反复诘问中警惕它的消退。
而日本呢?天皇制被保留,战犯换一身衣服继续掌权,宪法是美国写的,自卫队是“违宪”的——整个国家陷入一种“不负责任的体制”。布鲁玛在分析日本不能像德国那样悔罪的根本理由时,直奔主题地指出,“没有对政治责任,准确地说,是对战争与和平的责任的承担,日本就不可能产生一种面对过去的成熟态度。必须先有政治变革,接着才会有心态变化……因为只有一个新政府才能与战后秩序一刀两断,而这一秩序至今仍然受到战时政权的玷污”。
在追溯东京审判的历史时,布鲁玛引用日本政治理论家丸山真男的观点,战前的日本政府就处在“不负责任的体制”之下,有着三种政治性格:供人抬的“神轿”“官吏”和“浪人”。其中,“神轿”居于最高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象征,由“官吏”负责抬扛(比如节庆期间的抬神轿活动)。“神轿”是一种标志,但那些扛它的“官吏”才是掌握实权的人。然而,一干“官吏”——包括官僚、政客、海陆军将领——常常被最底层的“浪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这些人里有军事冒进分子、头脑发热的战地指挥官、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等暴力论者。
布鲁玛敏锐地看到,日本国内对南京大屠杀的看法和立场就涉及天皇制度。这是他从对南京大屠杀的多种说法中一点一点仔细剥离出来的。面对这些“理解”南京屠城的说法,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南京屠城是“在意识形态的教唆下”发生的,“侵略者杀死‘劣等民族’是符合神圣天皇旨意的”。否认南京大屠杀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认识问题,而是涉及维护天皇制度的合法性和权威。
为了在经历可怕的事情之后活下去,每个人会不自觉地筛选、重组自己的记忆。曾在南京驻扎的日本兵东史郎在暮年时,公布了自己的战争日记。他曾反思,审判是件好事,但日本人应该获准设立自己的军事法庭。令他尤其愤怒的是,一份名为《昭和天皇的独白》,这份记录于1946年、于1991年方才出版的小书。书中显示,天皇不仅对局势一清二楚,好战,还自私自利。东史郎说:“我们为他去打仗,我的朋友为他战死,他却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
曾遭苏联俘虏的日本兵小熊谦二,感慨自己参加的那场“圣战”:“明明一个人最大的问题是怎么样养家糊口,怎么样在物资短缺的情形下经营生计;但国家却告诉你人生最重要的事是为国牺牲,谋求一个非常远大崇高但也因此永远看不清的目标。你失去了凭自己的眼睛去了解时势的能力,疲倦得动不了大脑,那形式至上的爱国主义则是唯一剩给大家的思想工具。这时你不会去反省这场战争到底是怎么回事,它究竟对不对;你也不会去反抗那要你笑着送亲人去死的主义,拒绝它的聒噪。你只能麻木冷漠,劳形于生活压力与包围着你的宣传口号之间。”“我自己对国家有所怨恨,所谓的国家,与人心不同,只是一种无机的物质。”
这种无机物状态,源于日本始终无法与天皇制度完全切割。二战期间,德国犯下的是“反人类罪”,而日本犯下的则是战争罪行,厘清这一罪行的最大障碍,是天皇在战后日本政治制度中的位置。日本的浪漫民族主义核心是天皇,由于天皇的存在,日本的浪漫民族主义一直延续至今。德国放弃了这种浪漫民族主义,代之以“宪法民族主义”,甚至比许多其他西方国家更加坚持和强调人权和人的尊严。
“受害者”的“鸵鸟心态”
日本难以与过去断绝,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暧昧不明的政治体制——日本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法西斯”国家。“它既没有法西斯或国家社会主义执政党派,也没有希特勒式的元首。最接近这一角色的是天皇,但不管他有过哪些头衔,都算不上是法西斯独裁者。”
布鲁玛认为,日本没有德国那种明确的责任制度,在日本起作用的是上文所提的“不负责任的体制”,日本的指挥系统“根本就是一笔糊涂账。因此,尽管战后德国的纳粹领导层被一锅端,但反观日本,不过是少了几位海陆军将领罢了”。天皇是这个不负责任的体制中最大的“神轿”,“1945年后,麦克阿瑟将军选择保留的恰恰就是这种权威象征,这一最神圣的‘神轿’……利用帝制象征巩固自己的权力。结果,他扼杀了日本民主制度运转的希望,并严重扭曲了历史”。
既然要保留天皇的权威,“裕仁的过去就不能沾上任何污点;可以说,象征物必须和以其名义犯下的罪行撇清干系”。所以,东京审判时,裕仁天皇不仅逃脱了制裁,法庭甚至都不能传唤他出庭作证。日美两国达成协议,最高“神轿”不得受一丝牵连。这是一笔政治交易,牺牲了战争受害者的正义,其非正义的后果一直延续至今。
以天皇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架构与日本的民族记忆,共同构筑了一个双螺旋结构。只要天皇还摆在这个位置上,“日本人就会在坦白过去一事上扭扭捏捏。因为天皇对发生的一切均负有正式责任,而通过免除他的罪责,所有人都得到了赦免”。
在不负责任的日本政权主导下,日本人不是忘记历史,而是选择性记忆。从战前到战后,日本一直存在着“日本人领导亚洲对抗西方”的神话。日本人选择了“受害者”记忆的同时,他们消除了自己作为对亚洲其他国家人民“加害者”的记忆。他们牢记自己是原子弹的受害者,却模糊了南京大屠杀的加害者身份。广岛和平纪念馆成了“和平的麦加”,却绝口不提广岛本身曾是日军第二大本营。早在1894年,日本同中国打响“甲午战争”时,部队正是从广岛出发、开赴前线的,明治天皇也把指挥部搬到了广岛。
“日本是战争受害者”这个神话,能被日本不同意识形态的阵营所接受并各自作出解释,他们之间虽然有分歧和对立,却能在这个神话周围结成某种同盟的关系。日本的保守派把由美国主导的日本宪法视为对日本主权和尊严的侵犯,日本的左派虽然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但一样对美国抱有敌意,他们反美,认为冷战期间华盛顿干预了日本宪法第九款,迫使日本成为冷战冲突的帮凶。即使政治自由派也经常声称,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掷的两颗原子弹清洗了日本的战争罪孽,使日本人获得道德权利,可以“审判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这是一种精妙的心理机制: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就能逃避加害者的责任。布鲁玛批判日本特殊的“后见”做法,批判其经由选择性记忆维系伪善的和平主义认同。
当日本人把目光从广岛转向南京时,对历史的“鸵鸟心态”尤为明显。许多日本人否认有南京大屠杀,这与德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德国,只有极少数人不承认大屠杀。但在日本,相当庞大的保守势力坚持认为,对日军大规模屠杀中国平民的报道是夸大其词,平民伤亡是战争必然造成的结果。
日本年青一代对日军罪行的认识模糊而不完整,日本的教科书回避历史事实是一个主要原因。保守的教育部(文部省)和左派教师的争论对峙陷入僵局。德国教科书把对纳粹的抵抗提升到政治德性的高度,相比之下,在日本,当年支持战争的信仰价值观(神道教)和天皇制度至今仍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批判和否定。
对日本的行为,人们需要进行双重反思:将一己的罪孽消解在全人类的罪孽中,逃避承担自身罪孽的责任;而对和平主义的准宗教态度,又预先封闭了世俗化讨论的可能,仿佛阐释的意图本身就充满不道德。日本的“后见”态度表明,当记忆的留存本身成为一场政治、文化斗争,对何谓历史“真实”的把握极易走向片面,甚至从历史认知的环节中剥落。
布鲁玛对德日在战后反思的差别不是“历史化”的,而是有着明确的记忆伦理和人道价值取向,那就是,德国的悔罪是一种日本至今未能取得的政治成熟和道德进步。正如学者徐贲所评价:“布鲁玛要告诉那些抱怨民族弱点或以民族文化特色为借口的人,文化决定论和命定论都不应是历史发生的解释。”
当然,也有读者在读后感中反思:“德国人是否也在‘表演忏悔’?日本是否永远无法醒来?”也有批评者认为,布鲁玛是否过于理想化德国的“悔罪模式”,忽略了其内部的争议与反复?但无论如何,这本书至今仍在被阅读、被讨论、被引用。今天,它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一个民族心中的幽灵。
装睡的人叫不醒,不是因为睡得太深,而是因为醒来太痛。这本书,正是布鲁玛用笔尖轻轻敲击那个装睡者的肩膀——一次又一次,耐心而坚定。直到某一天,也许有人会愿意睁开眼,看看真实的世界。而我们能做的,尤其在这充满着不确定性的当下,就是站在真相和时间一边。
相关阅读:
1.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3.约翰·W·道尔《无情之战: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与强权》,中信出版集团
4.安德鲁·N·布坎南,《全球视野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31—1953)》,东方出版中心
本报实习生 董诗妮
1931年9月18日晚,日军自编自导炸毁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嫁祸于中国军队,突然袭击并侵占了沈阳城和东北30多座城市。这一天成为日本大规模武装侵华的开始,也是法西斯国家正式发动侵略之日。自此以后,直到1945年,中国大地惨遭侵略,暴行让无数生灵失去了生命。
如今,94年过去了。同样是二战侵略国、战败国,皆背负着沉重的历史罪责,战后德国和日本“应对”各自战时罪孽方式却不同:一个是以悔罪的方式承受责任;另一个则是以抵赖和健忘来躲避报应。
为何德国能“觉醒”,日本却始终“装睡”?荷兰作家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的《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一书,正围绕这一话题展开。它不是一本传统的历史著作,而是一部“政治游记”——作者穿梭于柏林与东京,广岛与奥斯威辛,教科书编辑部与战争纪念馆之间,用对话、观察、文化符号与集体记忆的碎片,拼出了一幅关于“罪与罚”的图景。
根源是“不负责任的体制”
布鲁玛想知道的不仅仅是历史本身,还有历史如何被记忆、被扭曲、被利用。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他走遍德国与日本,访谈学者、教师、政治家、老兵、艺术家,甚至右翼分子。他参加广岛和平纪念仪式,也参观柏林犹太博物馆;他听家永三郎讲述教科书诉讼三十年,也听保守派议员辩解“南京大屠杀是夸大”;他关注德日两国关于反思战争的书籍、戏剧、电影、电视节目。
最终,布鲁玛得出结论:德国与日本的差异,不是文化性的,而是政治性的。不是“罪文化”与“耻文化”的区别,而是宪政体制、教育理念、政治精英与公共讨论空间的差异。他拒绝用“文化差异”来简单解释一切,也没有步《菊与刀》作者本尼迪克特的旧路,不认为德国人天生有“罪感”、日本人天生有“耻感”。他指出:真正决定一个国家如何面对过去的,不是民族性,而是政治结构。
德国战后经历了政治制度的彻底重构,纳粹被彻底清算,宪法爱国主义取代了民族主义。尽管“竭力遗忘”与“无法哀悼”的心理也曾一度困扰德国人,但他们最终选择正视历史,用异常残酷的方式面对自己的记忆,“德国人的记忆就像一条巨大的舌头,一遍遍地舔舐,想要找出那颗隐隐作痛的坏牙”——不惮于留存,并且在反复诘问中警惕它的消退。
而日本呢?天皇制被保留,战犯换一身衣服继续掌权,宪法是美国写的,自卫队是“违宪”的——整个国家陷入一种“不负责任的体制”。布鲁玛在分析日本不能像德国那样悔罪的根本理由时,直奔主题地指出,“没有对政治责任,准确地说,是对战争与和平的责任的承担,日本就不可能产生一种面对过去的成熟态度。必须先有政治变革,接着才会有心态变化……因为只有一个新政府才能与战后秩序一刀两断,而这一秩序至今仍然受到战时政权的玷污”。
在追溯东京审判的历史时,布鲁玛引用日本政治理论家丸山真男的观点,战前的日本政府就处在“不负责任的体制”之下,有着三种政治性格:供人抬的“神轿”“官吏”和“浪人”。其中,“神轿”居于最高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象征,由“官吏”负责抬扛(比如节庆期间的抬神轿活动)。“神轿”是一种标志,但那些扛它的“官吏”才是掌握实权的人。然而,一干“官吏”——包括官僚、政客、海陆军将领——常常被最底层的“浪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这些人里有军事冒进分子、头脑发热的战地指挥官、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等暴力论者。
布鲁玛敏锐地看到,日本国内对南京大屠杀的看法和立场就涉及天皇制度。这是他从对南京大屠杀的多种说法中一点一点仔细剥离出来的。面对这些“理解”南京屠城的说法,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南京屠城是“在意识形态的教唆下”发生的,“侵略者杀死‘劣等民族’是符合神圣天皇旨意的”。否认南京大屠杀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认识问题,而是涉及维护天皇制度的合法性和权威。
为了在经历可怕的事情之后活下去,每个人会不自觉地筛选、重组自己的记忆。曾在南京驻扎的日本兵东史郎在暮年时,公布了自己的战争日记。他曾反思,审判是件好事,但日本人应该获准设立自己的军事法庭。令他尤其愤怒的是,一份名为《昭和天皇的独白》,这份记录于1946年、于1991年方才出版的小书。书中显示,天皇不仅对局势一清二楚,好战,还自私自利。东史郎说:“我们为他去打仗,我的朋友为他战死,他却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
曾遭苏联俘虏的日本兵小熊谦二,感慨自己参加的那场“圣战”:“明明一个人最大的问题是怎么样养家糊口,怎么样在物资短缺的情形下经营生计;但国家却告诉你人生最重要的事是为国牺牲,谋求一个非常远大崇高但也因此永远看不清的目标。你失去了凭自己的眼睛去了解时势的能力,疲倦得动不了大脑,那形式至上的爱国主义则是唯一剩给大家的思想工具。这时你不会去反省这场战争到底是怎么回事,它究竟对不对;你也不会去反抗那要你笑着送亲人去死的主义,拒绝它的聒噪。你只能麻木冷漠,劳形于生活压力与包围着你的宣传口号之间。”“我自己对国家有所怨恨,所谓的国家,与人心不同,只是一种无机的物质。”
这种无机物状态,源于日本始终无法与天皇制度完全切割。二战期间,德国犯下的是“反人类罪”,而日本犯下的则是战争罪行,厘清这一罪行的最大障碍,是天皇在战后日本政治制度中的位置。日本的浪漫民族主义核心是天皇,由于天皇的存在,日本的浪漫民族主义一直延续至今。德国放弃了这种浪漫民族主义,代之以“宪法民族主义”,甚至比许多其他西方国家更加坚持和强调人权和人的尊严。
“受害者”的“鸵鸟心态”
日本难以与过去断绝,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暧昧不明的政治体制——日本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法西斯”国家。“它既没有法西斯或国家社会主义执政党派,也没有希特勒式的元首。最接近这一角色的是天皇,但不管他有过哪些头衔,都算不上是法西斯独裁者。”
布鲁玛认为,日本没有德国那种明确的责任制度,在日本起作用的是上文所提的“不负责任的体制”,日本的指挥系统“根本就是一笔糊涂账。因此,尽管战后德国的纳粹领导层被一锅端,但反观日本,不过是少了几位海陆军将领罢了”。天皇是这个不负责任的体制中最大的“神轿”,“1945年后,麦克阿瑟将军选择保留的恰恰就是这种权威象征,这一最神圣的‘神轿’……利用帝制象征巩固自己的权力。结果,他扼杀了日本民主制度运转的希望,并严重扭曲了历史”。
既然要保留天皇的权威,“裕仁的过去就不能沾上任何污点;可以说,象征物必须和以其名义犯下的罪行撇清干系”。所以,东京审判时,裕仁天皇不仅逃脱了制裁,法庭甚至都不能传唤他出庭作证。日美两国达成协议,最高“神轿”不得受一丝牵连。这是一笔政治交易,牺牲了战争受害者的正义,其非正义的后果一直延续至今。
以天皇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架构与日本的民族记忆,共同构筑了一个双螺旋结构。只要天皇还摆在这个位置上,“日本人就会在坦白过去一事上扭扭捏捏。因为天皇对发生的一切均负有正式责任,而通过免除他的罪责,所有人都得到了赦免”。
在不负责任的日本政权主导下,日本人不是忘记历史,而是选择性记忆。从战前到战后,日本一直存在着“日本人领导亚洲对抗西方”的神话。日本人选择了“受害者”记忆的同时,他们消除了自己作为对亚洲其他国家人民“加害者”的记忆。他们牢记自己是原子弹的受害者,却模糊了南京大屠杀的加害者身份。广岛和平纪念馆成了“和平的麦加”,却绝口不提广岛本身曾是日军第二大本营。早在1894年,日本同中国打响“甲午战争”时,部队正是从广岛出发、开赴前线的,明治天皇也把指挥部搬到了广岛。
“日本是战争受害者”这个神话,能被日本不同意识形态的阵营所接受并各自作出解释,他们之间虽然有分歧和对立,却能在这个神话周围结成某种同盟的关系。日本的保守派把由美国主导的日本宪法视为对日本主权和尊严的侵犯,日本的左派虽然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但一样对美国抱有敌意,他们反美,认为冷战期间华盛顿干预了日本宪法第九款,迫使日本成为冷战冲突的帮凶。即使政治自由派也经常声称,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掷的两颗原子弹清洗了日本的战争罪孽,使日本人获得道德权利,可以“审判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这是一种精妙的心理机制: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就能逃避加害者的责任。布鲁玛批判日本特殊的“后见”做法,批判其经由选择性记忆维系伪善的和平主义认同。
当日本人把目光从广岛转向南京时,对历史的“鸵鸟心态”尤为明显。许多日本人否认有南京大屠杀,这与德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德国,只有极少数人不承认大屠杀。但在日本,相当庞大的保守势力坚持认为,对日军大规模屠杀中国平民的报道是夸大其词,平民伤亡是战争必然造成的结果。
日本年青一代对日军罪行的认识模糊而不完整,日本的教科书回避历史事实是一个主要原因。保守的教育部(文部省)和左派教师的争论对峙陷入僵局。德国教科书把对纳粹的抵抗提升到政治德性的高度,相比之下,在日本,当年支持战争的信仰价值观(神道教)和天皇制度至今仍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批判和否定。
对日本的行为,人们需要进行双重反思:将一己的罪孽消解在全人类的罪孽中,逃避承担自身罪孽的责任;而对和平主义的准宗教态度,又预先封闭了世俗化讨论的可能,仿佛阐释的意图本身就充满不道德。日本的“后见”态度表明,当记忆的留存本身成为一场政治、文化斗争,对何谓历史“真实”的把握极易走向片面,甚至从历史认知的环节中剥落。
布鲁玛对德日在战后反思的差别不是“历史化”的,而是有着明确的记忆伦理和人道价值取向,那就是,德国的悔罪是一种日本至今未能取得的政治成熟和道德进步。正如学者徐贲所评价:“布鲁玛要告诉那些抱怨民族弱点或以民族文化特色为借口的人,文化决定论和命定论都不应是历史发生的解释。”
当然,也有读者在读后感中反思:“德国人是否也在‘表演忏悔’?日本是否永远无法醒来?”也有批评者认为,布鲁玛是否过于理想化德国的“悔罪模式”,忽略了其内部的争议与反复?但无论如何,这本书至今仍在被阅读、被讨论、被引用。今天,它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一个民族心中的幽灵。
装睡的人叫不醒,不是因为睡得太深,而是因为醒来太痛。这本书,正是布鲁玛用笔尖轻轻敲击那个装睡者的肩膀——一次又一次,耐心而坚定。直到某一天,也许有人会愿意睁开眼,看看真实的世界。而我们能做的,尤其在这充满着不确定性的当下,就是站在真相和时间一边。
相关阅读:
1.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3.约翰·W·道尔《无情之战: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与强权》,中信出版集团
4.安德鲁·N·布坎南,《全球视野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31—1953)》,东方出版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