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学术东移,他起到了支柱作用。探寻他在齐鲁大地留下的一连串足迹,不仅能看见历史的轮廓,更能感受到那股追寻文明进步的力量——
大哉郑康成
2024-05-22
作者:
来源:
大众日报
 【 查看PDF版】
【 查看PDF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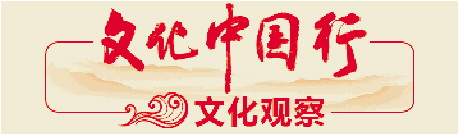 |
|
|
 |
|
|
□ 本报记者 卢昱
“大哉郑康成,探赜靡不举。六艺既该通,百家亦兼取。至今三礼存,其学非小补。”清初大学者顾炎武写的《述古诗》,对郑玄(字康成)的一生作了精彩概括。郑玄,北海高密人(现潍坊市峡山区郑公街道),生于东汉顺帝永建二年(公元127年),卒于汉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
郑康成之大,在于他既赅通六艺,又对古今文经学兼收并蓄,择善而从。《后汉书·郑玄列传》记载,郑玄一生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再加上其他著作,凡百余万言,是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汉末学术东移,他起到了支柱作用。
1967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发掘阿斯塔那第363号墓葬时,发现一份长达5.2米的长卷,是唐中宗景龙四年(公元710年)私塾学生卜天寿抄写的郑氏注《论语》作业,从《为政第二》哀公问曰章到《公冶长第五》,凡177行,其中部分有朱笔圈点涂改。这份作业十分重要,因为郑玄的《论语》注本,在宋代以后就散佚了,通过卜天寿的作业,得以恢复了将近1/5的篇幅,这是儒家经典史上的大事。由此可见,郑玄的影响力之大,穿越古今。郑玄在齐鲁大地留下一连串的足迹,探寻其行走的路线,不仅能看见历史的轮廓,更能感受到那股追寻文明进步的力量。
郑生今去,吾道东矣
公元127年,郑玄在潍水河畔呱呱坠地。宋代《太平寰宇记》中引用唐《郡国志》的记载曰:“密州高密西有郑玄宅,亦曰‘郑城’。玄后移葬于砺阜,墓侧有稻田万顷。断水造鱼梁,岁收亿万,号万匹梁。”鱼梁是古人在河流或海水出口处,筑堰拦水捕鱼的一种设施,多用木桩、柴枝或编网等制成篱笆或栅栏,水可以照常流过,但鱼、虾、蟹等都会被拦截下来。当时的稻城居民,不仅利用潍水蓄塘种植水稻,也用水稻秸秆造鱼梁。
“稻城的故址,大约在今天峡山区城子村附近。”潍坊市峡山区郑公街道文化站学者谢美龙介绍,今城子村西南有古城遗址,水城村西南、西北均有古文化遗址,其中村西北遗址文化层上限至龙山文化(距今约4500年-4000年前)。
郑玄天资聪颖,但因家贫,在成年后,不得不担任乡啬夫(专管收敛赋税的地方小官)。虽已步入官场,郑玄却不为官运奔波,而是求学之志不衰,只要有空闲就去找郡县学官问学。
北海郡太守杜密推荐郑玄到京城太学受业。求学若渴的郑玄学无常师,到处求教于“处逸大儒”。他先是拜京兆尹第五元先生门下,学习《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等。后来,他又师从东郡张恭祖,攻读《周官》《左氏春秋》《古文尚书》《韩诗》《礼记》等。他“游学于周秦之都(今洛阳、西安一带),往来于幽、并、兖、豫之域”,遍访贤者,学业渐成。
34岁这年,郑玄感到“山东无足问者”,便西出函谷关,经涿郡卢植介绍,拜关中大儒马融为师,学习古文经。马融当时名气很大,“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近者五十余生”。“郑玄在马融门下学了三年,却一直没听到马融当面授课,只能跟着马融门下高徒学习。尽管如此,郑玄也不曾懈怠,每日苦学。”谢美龙说。
据《后汉书·郑玄列传》记载,一天,马融正和高徒们讨论图纬问题,因涉及天文计算,一时无人能解。卢植趁机推荐说,郑康成习《九章算术》甚精,何不请来一试?马融虽记不起郑玄为何人,但同意请来一试。郑玄以“勾股割圆”法则,解决了马融等遇到的天文计算难题,众高徒心服口服,郑玄赢得了马融的信赖和器重,从此进入高徒行列。在马融门下学习了七年,郑玄回家尽孝。望着弟子东去的背影,马融感叹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
在淄川,也有康成书院、郑康成庙、晒书台等诸多遗迹。嘉靖《淄川县志》载:“康成书院在县东梓橦山十里许,书院之设不知起于何年,岂郑公关中得道东归,其齐地生徒讲道而设耶?”“郑公书院”是明清淄川八景之一。道光《济南府志·古迹·淄川》说:“郑康成书院,县志云:在黉山之阳,为邑景之一。晒书台,通志云:在县东北十二里黉山之麓。旧志云:在黉山畔。《三齐略记》云:郑康成刊注诗书日,栖迟于此,台畔有草,如薤而长,曰书带草。”
东汉桓帝、灵帝时代,士大夫、贵族遭“党事”而被禁锢。郑玄因是北海郡太守杜密的故吏,也被禁锢整整14年。这期间,郑玄家里还很贫穷,只得“客耕东莱”,一面种田维持生计,一面教授门徒。此时,他打破了经学的家法,注释与著书“几百余万言”,创立了郑学。据说当时京师之人称何休为“学海”,而称郑玄为“经神”,郑玄的声望远超过何休。当时不少求学者不远千里投到郑玄门下,一时间郑玄桃李满门。
党禁解后,各方势力都想利用郑玄,以达到争取士人和百姓支持的目的。据资料统计,郑玄“辞征辟”前后有十四次之多,皆不就,专心注经。
东汉末北海相孔融,仰慕郑玄,引太史公、商山四皓的典故尊称郑玄为“郑公”,仿古制告谕高密县为郑玄立“郑公乡”,立“通德门”。通德门立后,郑玄故里改为“通德里”,后世史书多称郑玄“高密县郑公乡通德里人”,后世当地文人也多以“郑公乡人”“通德里”自居。当时安丘、寿光等地名士也俨然把郑玄作为安丘人,并引以为豪。明代以来,以郑玄祠墓、郑公乡、砺阜山为文化元素的盛景“德里流芳”,甚至成为“安丘八景”之一。
追随先哲,可谓磊落
郑玄曾游学四方,从事经学教育三十余载,培养弟子上万人,其中不少成为大官或名士。如御史大夫郗虑、尚书崔琰、魏郡太守国渊,以及刘备的重臣孙乾等。《三国演义》称刘备亦曾拜郑玄为师,在《华阳国志·刘后主志》载有诸葛亮的一段话:“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语赦也。’”据此可知,郑玄在徐州时与刘备关系密切,相当于刘备的师友,刘备经常向他请教“治乱之道”。蜀国大将姜维和魏国大臣王基,则是郑玄的“再传弟子”。
汉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黄巾军攻占北海,为了不让生徒辍学,郑玄到崂山西北部的不其山下继续办学,后来不其山地带也被占领。郑玄无奈只得远去徐州,到陶谦那里,一来避黄巾之乱,同时找个安定治学的处所。在徐州时,陶谦意欲要他为幕僚,享受俸禄,他再三辞谢。由此,在山东许多地方流传着郑玄的传说,方志中关于康成书院、康成讲堂的记载也屡见不鲜。
郑玄曾在即墨不其山下讲学,即墨人对郑玄的追慕情结传承千年不衰。元代于钦《齐乘》云:“劳山、不其皆郑康成讲学之地,文泽涵濡,草木之秀异,千载之下,第茅塞焉,深可叹已。”明黄宗昌《崂山志》亦载:“不其山下昔有康成书院,有草生,大如薤(xiè),叶长尺余,坚劲异常。草,人谓是康成书带草也。”
在今峡山区郑公祠的后院中,也种植着一片书带草。当年,郑玄正是用书带草的长叶捆扎书简。在他的眼里,纷繁杂乱的书简被叶脉清晰的书带草串联起来,行行文字也如书带草,从容地延伸着,传递着儒学的永恒魅力。郑玄所作的种种努力,如同书带草的生长趋向。
清初顾炎武游历即墨时,康成书院早已不存。其《不其山》诗云:“荒山书院有人耕,不记山名与县名。为问黄巾满天下,可能容得郑康成。”相传,郑玄讲学注重实践,为了讲授《三礼》,他与弟子开辟出一块空地,取名为演礼场,并制作了道具,让弟子按经书上记载去演示。在郑玄讲学的地方,留下了“书院村”“演礼”等地名,沿用至今。书院村附近有两座山,一为可乐山,原名窠落山,相传郑玄多次来此登高远眺,东观日出,环顾群山,不亦乐乎,山因此而得名;另一山名为扎彩山,据说是郑玄庆祝扎彩门之地。
在平邑县,也有多处与郑玄相关的遗迹。《太平御览》对郑玄避难南城的事迹有着详尽的叙述:“郑玄汉末遭黄巾之难,客于徐州。今《孝经序》,郑氏所作。其序云:仆避于南城之山,栖迟岩石之下,念昔先人余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经》。盖康成微逊时所作也。今西上可二里所,有石室焉,周回五丈。俗云是康成注《孝经》处也”。郑玄之所以选择在此落脚,因为这里是曾子葬父处,亦名曾子山,郑玄在此注曾子所著《孝经》,其追随先哲之意可谓磊落。郑玄去世后,当地人为了纪念他,将其避难之地命名为“郑城”,亦名“郑司农城”,并将其衣冠葬于郑城镇康成庄西北的松林村东岭,原名“郑玄坟”,后讹传为“郑仙坟”。
一生追随孔子足迹
在威海市文登区,也有康成讲堂遗迹。雍正《山东通志》载:“长学山在县西四十里,汉郑康成授徒于此,有书堂遗址焉。”光绪《文登县志》载:“长学山在城西四十里,汉郑康成隐此教授生徒,有康成讲堂,今为圣皇庙。”文登人对郑玄这位异乡先贤给予了极高礼遇,清代将郑玄供奉文登县乡贤祠。
郑玄一生治经,追随孔子的足迹,努力接近孔子的高度。他曾不止一次梦见自己手执丹漆之礼器,像先人郑国一样,为孔子的弟子,跟在孔子的身后,学礼治经。晚年的郑玄在注释《论语》时,已特别注意解说孔子言行的背景,即剥离了各种《论语》谶的比附、神化,展示出了一位切实、活泼生动的长者形象,一个更趋坦诚、真实的孔子形象。
如郑玄对《述而》“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的注释,就只是强调孔子“习读不敢懈倦”“汲汲然,自恐不能究竟其意”而带来的对未来的一丝隐忧和恐惧。这更符合孔子的生活实际,也把孔子从云间拉到地上,一变昔日扑朔迷离的神化色泽,是一位蔼如的智者。
郑玄74岁这年春天,又梦见孔子。他意识到将与这个世界告别了。此时,袁绍与曹操对峙于黄河之畔的官渡,一场大战一触即发。袁绍为了壮大己方声势,令其子袁谭(时为青州牧),采取“绑架”似的手段,逼迫郑玄随军。郑玄迫不得已,“载病”上路。此时,他的《易》尚未注完,一路颠簸一路注《易》,行至河北元城,病情加重,只好停下治病。次年六月,郑玄病卒。此时,《易》刚好注完。
郑玄生前留下薄葬遗嘱,参加葬礼的自郡守以下门生弟子过千人。郑玄初葬剧东(今青州郑母镇),后因墓毁,归葬高密砺阜山下郑氏祖茔。郑玄墓现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前有清乾隆十四年镌刻的“郑康成先生之墓”石碑。墓西南有郑公祠堂三间。堂前偏西,有一株老柏树,相传为郑玄手植,虽早枯死,但姿态如虬龙,疏朗而奇绝。
“大哉郑康成,探赜靡不举。六艺既该通,百家亦兼取。至今三礼存,其学非小补。”清初大学者顾炎武写的《述古诗》,对郑玄(字康成)的一生作了精彩概括。郑玄,北海高密人(现潍坊市峡山区郑公街道),生于东汉顺帝永建二年(公元127年),卒于汉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
郑康成之大,在于他既赅通六艺,又对古今文经学兼收并蓄,择善而从。《后汉书·郑玄列传》记载,郑玄一生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再加上其他著作,凡百余万言,是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汉末学术东移,他起到了支柱作用。
1967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发掘阿斯塔那第363号墓葬时,发现一份长达5.2米的长卷,是唐中宗景龙四年(公元710年)私塾学生卜天寿抄写的郑氏注《论语》作业,从《为政第二》哀公问曰章到《公冶长第五》,凡177行,其中部分有朱笔圈点涂改。这份作业十分重要,因为郑玄的《论语》注本,在宋代以后就散佚了,通过卜天寿的作业,得以恢复了将近1/5的篇幅,这是儒家经典史上的大事。由此可见,郑玄的影响力之大,穿越古今。郑玄在齐鲁大地留下一连串的足迹,探寻其行走的路线,不仅能看见历史的轮廓,更能感受到那股追寻文明进步的力量。
郑生今去,吾道东矣
公元127年,郑玄在潍水河畔呱呱坠地。宋代《太平寰宇记》中引用唐《郡国志》的记载曰:“密州高密西有郑玄宅,亦曰‘郑城’。玄后移葬于砺阜,墓侧有稻田万顷。断水造鱼梁,岁收亿万,号万匹梁。”鱼梁是古人在河流或海水出口处,筑堰拦水捕鱼的一种设施,多用木桩、柴枝或编网等制成篱笆或栅栏,水可以照常流过,但鱼、虾、蟹等都会被拦截下来。当时的稻城居民,不仅利用潍水蓄塘种植水稻,也用水稻秸秆造鱼梁。
“稻城的故址,大约在今天峡山区城子村附近。”潍坊市峡山区郑公街道文化站学者谢美龙介绍,今城子村西南有古城遗址,水城村西南、西北均有古文化遗址,其中村西北遗址文化层上限至龙山文化(距今约4500年-4000年前)。
郑玄天资聪颖,但因家贫,在成年后,不得不担任乡啬夫(专管收敛赋税的地方小官)。虽已步入官场,郑玄却不为官运奔波,而是求学之志不衰,只要有空闲就去找郡县学官问学。
北海郡太守杜密推荐郑玄到京城太学受业。求学若渴的郑玄学无常师,到处求教于“处逸大儒”。他先是拜京兆尹第五元先生门下,学习《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等。后来,他又师从东郡张恭祖,攻读《周官》《左氏春秋》《古文尚书》《韩诗》《礼记》等。他“游学于周秦之都(今洛阳、西安一带),往来于幽、并、兖、豫之域”,遍访贤者,学业渐成。
34岁这年,郑玄感到“山东无足问者”,便西出函谷关,经涿郡卢植介绍,拜关中大儒马融为师,学习古文经。马融当时名气很大,“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近者五十余生”。“郑玄在马融门下学了三年,却一直没听到马融当面授课,只能跟着马融门下高徒学习。尽管如此,郑玄也不曾懈怠,每日苦学。”谢美龙说。
据《后汉书·郑玄列传》记载,一天,马融正和高徒们讨论图纬问题,因涉及天文计算,一时无人能解。卢植趁机推荐说,郑康成习《九章算术》甚精,何不请来一试?马融虽记不起郑玄为何人,但同意请来一试。郑玄以“勾股割圆”法则,解决了马融等遇到的天文计算难题,众高徒心服口服,郑玄赢得了马融的信赖和器重,从此进入高徒行列。在马融门下学习了七年,郑玄回家尽孝。望着弟子东去的背影,马融感叹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
在淄川,也有康成书院、郑康成庙、晒书台等诸多遗迹。嘉靖《淄川县志》载:“康成书院在县东梓橦山十里许,书院之设不知起于何年,岂郑公关中得道东归,其齐地生徒讲道而设耶?”“郑公书院”是明清淄川八景之一。道光《济南府志·古迹·淄川》说:“郑康成书院,县志云:在黉山之阳,为邑景之一。晒书台,通志云:在县东北十二里黉山之麓。旧志云:在黉山畔。《三齐略记》云:郑康成刊注诗书日,栖迟于此,台畔有草,如薤而长,曰书带草。”
东汉桓帝、灵帝时代,士大夫、贵族遭“党事”而被禁锢。郑玄因是北海郡太守杜密的故吏,也被禁锢整整14年。这期间,郑玄家里还很贫穷,只得“客耕东莱”,一面种田维持生计,一面教授门徒。此时,他打破了经学的家法,注释与著书“几百余万言”,创立了郑学。据说当时京师之人称何休为“学海”,而称郑玄为“经神”,郑玄的声望远超过何休。当时不少求学者不远千里投到郑玄门下,一时间郑玄桃李满门。
党禁解后,各方势力都想利用郑玄,以达到争取士人和百姓支持的目的。据资料统计,郑玄“辞征辟”前后有十四次之多,皆不就,专心注经。
东汉末北海相孔融,仰慕郑玄,引太史公、商山四皓的典故尊称郑玄为“郑公”,仿古制告谕高密县为郑玄立“郑公乡”,立“通德门”。通德门立后,郑玄故里改为“通德里”,后世史书多称郑玄“高密县郑公乡通德里人”,后世当地文人也多以“郑公乡人”“通德里”自居。当时安丘、寿光等地名士也俨然把郑玄作为安丘人,并引以为豪。明代以来,以郑玄祠墓、郑公乡、砺阜山为文化元素的盛景“德里流芳”,甚至成为“安丘八景”之一。
追随先哲,可谓磊落
郑玄曾游学四方,从事经学教育三十余载,培养弟子上万人,其中不少成为大官或名士。如御史大夫郗虑、尚书崔琰、魏郡太守国渊,以及刘备的重臣孙乾等。《三国演义》称刘备亦曾拜郑玄为师,在《华阳国志·刘后主志》载有诸葛亮的一段话:“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语赦也。’”据此可知,郑玄在徐州时与刘备关系密切,相当于刘备的师友,刘备经常向他请教“治乱之道”。蜀国大将姜维和魏国大臣王基,则是郑玄的“再传弟子”。
汉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黄巾军攻占北海,为了不让生徒辍学,郑玄到崂山西北部的不其山下继续办学,后来不其山地带也被占领。郑玄无奈只得远去徐州,到陶谦那里,一来避黄巾之乱,同时找个安定治学的处所。在徐州时,陶谦意欲要他为幕僚,享受俸禄,他再三辞谢。由此,在山东许多地方流传着郑玄的传说,方志中关于康成书院、康成讲堂的记载也屡见不鲜。
郑玄曾在即墨不其山下讲学,即墨人对郑玄的追慕情结传承千年不衰。元代于钦《齐乘》云:“劳山、不其皆郑康成讲学之地,文泽涵濡,草木之秀异,千载之下,第茅塞焉,深可叹已。”明黄宗昌《崂山志》亦载:“不其山下昔有康成书院,有草生,大如薤(xiè),叶长尺余,坚劲异常。草,人谓是康成书带草也。”
在今峡山区郑公祠的后院中,也种植着一片书带草。当年,郑玄正是用书带草的长叶捆扎书简。在他的眼里,纷繁杂乱的书简被叶脉清晰的书带草串联起来,行行文字也如书带草,从容地延伸着,传递着儒学的永恒魅力。郑玄所作的种种努力,如同书带草的生长趋向。
清初顾炎武游历即墨时,康成书院早已不存。其《不其山》诗云:“荒山书院有人耕,不记山名与县名。为问黄巾满天下,可能容得郑康成。”相传,郑玄讲学注重实践,为了讲授《三礼》,他与弟子开辟出一块空地,取名为演礼场,并制作了道具,让弟子按经书上记载去演示。在郑玄讲学的地方,留下了“书院村”“演礼”等地名,沿用至今。书院村附近有两座山,一为可乐山,原名窠落山,相传郑玄多次来此登高远眺,东观日出,环顾群山,不亦乐乎,山因此而得名;另一山名为扎彩山,据说是郑玄庆祝扎彩门之地。
在平邑县,也有多处与郑玄相关的遗迹。《太平御览》对郑玄避难南城的事迹有着详尽的叙述:“郑玄汉末遭黄巾之难,客于徐州。今《孝经序》,郑氏所作。其序云:仆避于南城之山,栖迟岩石之下,念昔先人余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经》。盖康成微逊时所作也。今西上可二里所,有石室焉,周回五丈。俗云是康成注《孝经》处也”。郑玄之所以选择在此落脚,因为这里是曾子葬父处,亦名曾子山,郑玄在此注曾子所著《孝经》,其追随先哲之意可谓磊落。郑玄去世后,当地人为了纪念他,将其避难之地命名为“郑城”,亦名“郑司农城”,并将其衣冠葬于郑城镇康成庄西北的松林村东岭,原名“郑玄坟”,后讹传为“郑仙坟”。
一生追随孔子足迹
在威海市文登区,也有康成讲堂遗迹。雍正《山东通志》载:“长学山在县西四十里,汉郑康成授徒于此,有书堂遗址焉。”光绪《文登县志》载:“长学山在城西四十里,汉郑康成隐此教授生徒,有康成讲堂,今为圣皇庙。”文登人对郑玄这位异乡先贤给予了极高礼遇,清代将郑玄供奉文登县乡贤祠。
郑玄一生治经,追随孔子的足迹,努力接近孔子的高度。他曾不止一次梦见自己手执丹漆之礼器,像先人郑国一样,为孔子的弟子,跟在孔子的身后,学礼治经。晚年的郑玄在注释《论语》时,已特别注意解说孔子言行的背景,即剥离了各种《论语》谶的比附、神化,展示出了一位切实、活泼生动的长者形象,一个更趋坦诚、真实的孔子形象。
如郑玄对《述而》“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的注释,就只是强调孔子“习读不敢懈倦”“汲汲然,自恐不能究竟其意”而带来的对未来的一丝隐忧和恐惧。这更符合孔子的生活实际,也把孔子从云间拉到地上,一变昔日扑朔迷离的神化色泽,是一位蔼如的智者。
郑玄74岁这年春天,又梦见孔子。他意识到将与这个世界告别了。此时,袁绍与曹操对峙于黄河之畔的官渡,一场大战一触即发。袁绍为了壮大己方声势,令其子袁谭(时为青州牧),采取“绑架”似的手段,逼迫郑玄随军。郑玄迫不得已,“载病”上路。此时,他的《易》尚未注完,一路颠簸一路注《易》,行至河北元城,病情加重,只好停下治病。次年六月,郑玄病卒。此时,《易》刚好注完。
郑玄生前留下薄葬遗嘱,参加葬礼的自郡守以下门生弟子过千人。郑玄初葬剧东(今青州郑母镇),后因墓毁,归葬高密砺阜山下郑氏祖茔。郑玄墓现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前有清乾隆十四年镌刻的“郑康成先生之墓”石碑。墓西南有郑公祠堂三间。堂前偏西,有一株老柏树,相传为郑玄手植,虽早枯死,但姿态如虬龙,疏朗而奇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