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封家书谈起
2024-04-07
作者:
来源:
大众日报
 【 查看PDF版】
【 查看PDF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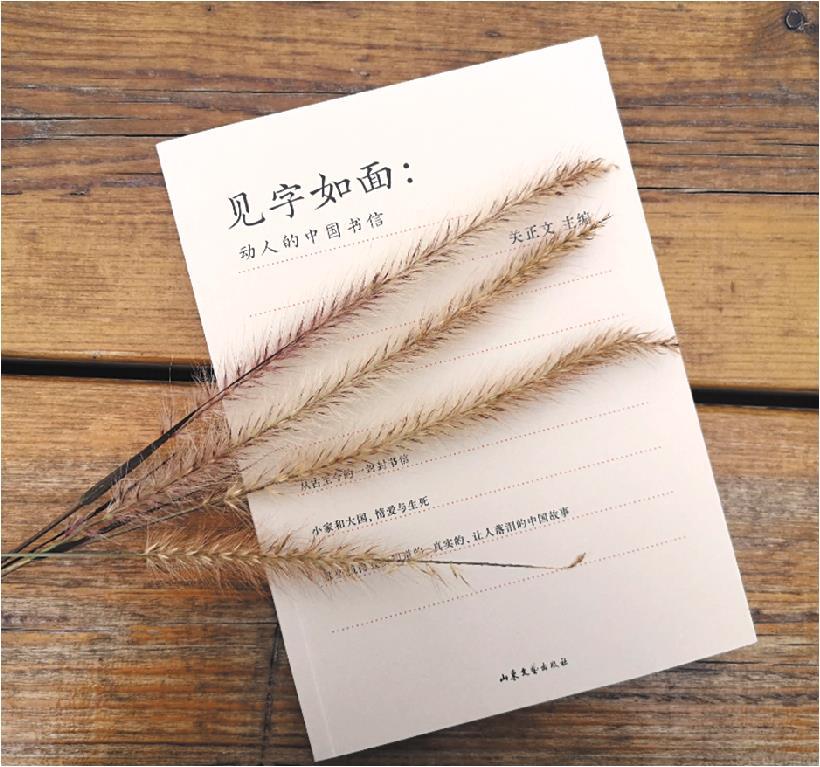 |
|
|
□ 郭万保
十六世纪九十年代的一天,山东新城县一户人家里,母亲徐氏给远在浙江山阴县任知县的儿子耿庭柏写了封家信。时隔400多年,这封信的具体内容已不得而知,但信中一首《寄子诗》却流传至今:“家内平安报尔知,田园岁入有余资。丝毫不用南中物,好作清官答圣时。”这首诗的意思平白如话,既报家中平安富足,又叮嘱儿子清廉为官,其蕴含的真挚浓烈的亲情、为政清廉的意识以及重要教育意义深刻而隽永。
徐氏自幼聪慧,诗才颇高,同时德行佳美,处事果断,生活节俭,乐善好施。其新城同乡、时任江西道监察御史王象蒙称其“遇事剖决,有丈夫风,乐捐济,好淡素,绮纨弗御,甘脆弗进”。徐氏之子耿庭柏,字惟芬,号华平,勤奋好学,德才俱佳。1591年,20岁的他中山东乡试亚元,第二年中进士,由此步入仕途,历任山阴县知县、光山县知县、兵部职方司主事、吏部考功司主事、吏部验封司郎中、吏部文选司郎中、太常寺少卿等职。1622年他被提拔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浙江巡抚。耿庭柏牢记母亲殷殷教诲,一生廉洁勤政,以民为重,恪尽职守,功绩卓著,1623年52岁时病逝于浙江巡抚任上。
实际上,耿庭柏的成就不仅受益于母亲的彤管慈教,而且承继于其父亲耿鸣世的率先垂范。耿鸣世于1568年中进士,历任河北邢台县知县,刑部主事,广西、山西监察御史,陕甘巡按兼提学使,南京、应天等六府巡按,蒲州通判,潞安府推官,礼部员外郎,陕西陇右道佥事、布政使司右参议。从政20多年,他始终正气凛然,清廉自守,鞠躬尽瘁,深受民众爱戴,成为百官之典范。时人有诗赞之云:“问公遗后何所以,一线清风在乡里。”又云:“嗟乎耿夫子,正气凌九霄。”
可以说,正是父母言传身教,逐渐形成良好的家教家风并得以有效代际传承,一个家庭家族才能够持久兴盛、家业绵长。新城耿氏家族的后续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与耿鸣世、耿庭柏父子同时及之后,明清时期耿氏家族有5人考中进士步入仕途,或担任朝廷要员,或成为封疆大吏,且都清正廉明,政绩卓显,耿氏家族遂成为当地声名显赫的高门望族。清中期以后,新城耿氏家族逐渐以商贾为业,工厂和店铺遍布济南、张店、周村等地,诚信经营,童叟无欺,且积极参与捐建学堂、修桥铺路、周济灾民等泽被乡里的慈善事业,续写了家族辉煌。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优良的家教家风必以德行为重。因此“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联语自古便广为流传。在众多嘉德懿行中,清正廉洁、勤政为民尤为人们所看重。在这方面,新城王氏家族的家教家风同样可圈可点。明嘉靖时期,先后任工部主事、户部员外郎等职的王重光首立“道义读书”家训,后世不断传承发展。清初,一代诗宗、官至刑部尚书的王渔洋在仕宦生涯中,自觉践行“不负民即不负国,不负国即不负所学”的为官之道,洁己爱民、宽政慎行,被誉为“一代廉吏”。1697年,其三子王启汸出任唐山县令,王渔洋亲书《手镜》箴言50条,教育他做一个“清慎勤”的好官。正是这种以“忠勤报国,洁己爱民”为核心精神的家教家风浸染影响,明清时期新城王氏家族出进士30人、举人52人,从政的110多人中,官至尚书、御史、侍郎、总督、巡抚等三品以上朝廷重臣的9人,还有众多家族成员担任中等要职,故有“新城王半朝”之誉。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纵观历史,那些“积不善”而殃及子孙的也代不乏人。被《宋史》列入“奸臣传”、因陷害岳飞留下千古骂名的秦桧,在家风建设方面同样乏善可陈。1153年,秦桧之孙秦埙参加南宋朝廷组织的“锁厅试”。秦桧事先把主考官陈之茂请到相府,希望他将秦埙录为第一名。清正刚直的陈之茂坚持以文章质量区分优劣,最终定才名远播的陆游为第一名,把秦埙置于第二名。秦桧对此怀恨在心,第二年陆游参加殿试即遭“显黜”,此后陈之茂也“几蹈危机”。1752年,高中状元的秦大士与袁枚等人一起游览杭州西湖,看到岳飞墓前秦桧夫妇等人的跪像,袁枚便出一上联:人从宋后羞名桧;秦大士脸色一红随即对道:我到坟前愧姓秦。
古今一理,“正家而天下定矣”。不论社会和时代如何变迁,不论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多大变化,家教家风始终是家庭建设的核心内容和社会建设的基础工程,关系着个人的健康成长和家庭的幸福安宁,也关系到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稳定。好的家教家风能够引领人向上向善,使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并促进社会和谐文明进步;家风不良则会祸及子孙,贻害无穷。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同志特别注重家教家风建设。他把“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原则融入生活中的一点一滴、每时每刻,并要求妻子和儿女不占公家一点便宜。他在临终时嘱托妻子徐俊雅:“我死后,你会很难,但日子再苦再难也不要伸手向组织要补助、要救济”。徐俊雅坚守和践行着丈夫的遗训,告诫孩子们:“焦裕禄的家人这个名号,我们全家要当得起,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当得起。”焦家6个子女始终为人低调务实,严于律己,二女儿焦守云曾说:“父亲教育我们不能搞特殊,但做焦裕禄的孩子,又的确很‘特殊’——我们必须耐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贫。”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庭和睦、家教良好、家风端正,子女才能健康成长,社会才能健康发展。这也是400多年前徐氏《寄子诗》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十六世纪九十年代的一天,山东新城县一户人家里,母亲徐氏给远在浙江山阴县任知县的儿子耿庭柏写了封家信。时隔400多年,这封信的具体内容已不得而知,但信中一首《寄子诗》却流传至今:“家内平安报尔知,田园岁入有余资。丝毫不用南中物,好作清官答圣时。”这首诗的意思平白如话,既报家中平安富足,又叮嘱儿子清廉为官,其蕴含的真挚浓烈的亲情、为政清廉的意识以及重要教育意义深刻而隽永。
徐氏自幼聪慧,诗才颇高,同时德行佳美,处事果断,生活节俭,乐善好施。其新城同乡、时任江西道监察御史王象蒙称其“遇事剖决,有丈夫风,乐捐济,好淡素,绮纨弗御,甘脆弗进”。徐氏之子耿庭柏,字惟芬,号华平,勤奋好学,德才俱佳。1591年,20岁的他中山东乡试亚元,第二年中进士,由此步入仕途,历任山阴县知县、光山县知县、兵部职方司主事、吏部考功司主事、吏部验封司郎中、吏部文选司郎中、太常寺少卿等职。1622年他被提拔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浙江巡抚。耿庭柏牢记母亲殷殷教诲,一生廉洁勤政,以民为重,恪尽职守,功绩卓著,1623年52岁时病逝于浙江巡抚任上。
实际上,耿庭柏的成就不仅受益于母亲的彤管慈教,而且承继于其父亲耿鸣世的率先垂范。耿鸣世于1568年中进士,历任河北邢台县知县,刑部主事,广西、山西监察御史,陕甘巡按兼提学使,南京、应天等六府巡按,蒲州通判,潞安府推官,礼部员外郎,陕西陇右道佥事、布政使司右参议。从政20多年,他始终正气凛然,清廉自守,鞠躬尽瘁,深受民众爱戴,成为百官之典范。时人有诗赞之云:“问公遗后何所以,一线清风在乡里。”又云:“嗟乎耿夫子,正气凌九霄。”
可以说,正是父母言传身教,逐渐形成良好的家教家风并得以有效代际传承,一个家庭家族才能够持久兴盛、家业绵长。新城耿氏家族的后续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与耿鸣世、耿庭柏父子同时及之后,明清时期耿氏家族有5人考中进士步入仕途,或担任朝廷要员,或成为封疆大吏,且都清正廉明,政绩卓显,耿氏家族遂成为当地声名显赫的高门望族。清中期以后,新城耿氏家族逐渐以商贾为业,工厂和店铺遍布济南、张店、周村等地,诚信经营,童叟无欺,且积极参与捐建学堂、修桥铺路、周济灾民等泽被乡里的慈善事业,续写了家族辉煌。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优良的家教家风必以德行为重。因此“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联语自古便广为流传。在众多嘉德懿行中,清正廉洁、勤政为民尤为人们所看重。在这方面,新城王氏家族的家教家风同样可圈可点。明嘉靖时期,先后任工部主事、户部员外郎等职的王重光首立“道义读书”家训,后世不断传承发展。清初,一代诗宗、官至刑部尚书的王渔洋在仕宦生涯中,自觉践行“不负民即不负国,不负国即不负所学”的为官之道,洁己爱民、宽政慎行,被誉为“一代廉吏”。1697年,其三子王启汸出任唐山县令,王渔洋亲书《手镜》箴言50条,教育他做一个“清慎勤”的好官。正是这种以“忠勤报国,洁己爱民”为核心精神的家教家风浸染影响,明清时期新城王氏家族出进士30人、举人52人,从政的110多人中,官至尚书、御史、侍郎、总督、巡抚等三品以上朝廷重臣的9人,还有众多家族成员担任中等要职,故有“新城王半朝”之誉。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纵观历史,那些“积不善”而殃及子孙的也代不乏人。被《宋史》列入“奸臣传”、因陷害岳飞留下千古骂名的秦桧,在家风建设方面同样乏善可陈。1153年,秦桧之孙秦埙参加南宋朝廷组织的“锁厅试”。秦桧事先把主考官陈之茂请到相府,希望他将秦埙录为第一名。清正刚直的陈之茂坚持以文章质量区分优劣,最终定才名远播的陆游为第一名,把秦埙置于第二名。秦桧对此怀恨在心,第二年陆游参加殿试即遭“显黜”,此后陈之茂也“几蹈危机”。1752年,高中状元的秦大士与袁枚等人一起游览杭州西湖,看到岳飞墓前秦桧夫妇等人的跪像,袁枚便出一上联:人从宋后羞名桧;秦大士脸色一红随即对道:我到坟前愧姓秦。
古今一理,“正家而天下定矣”。不论社会和时代如何变迁,不论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多大变化,家教家风始终是家庭建设的核心内容和社会建设的基础工程,关系着个人的健康成长和家庭的幸福安宁,也关系到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稳定。好的家教家风能够引领人向上向善,使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并促进社会和谐文明进步;家风不良则会祸及子孙,贻害无穷。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同志特别注重家教家风建设。他把“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原则融入生活中的一点一滴、每时每刻,并要求妻子和儿女不占公家一点便宜。他在临终时嘱托妻子徐俊雅:“我死后,你会很难,但日子再苦再难也不要伸手向组织要补助、要救济”。徐俊雅坚守和践行着丈夫的遗训,告诫孩子们:“焦裕禄的家人这个名号,我们全家要当得起,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当得起。”焦家6个子女始终为人低调务实,严于律己,二女儿焦守云曾说:“父亲教育我们不能搞特殊,但做焦裕禄的孩子,又的确很‘特殊’——我们必须耐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贫。”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庭和睦、家教良好、家风端正,子女才能健康成长,社会才能健康发展。这也是400多年前徐氏《寄子诗》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