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图》何图?
2023-08-06
作者:
来源:
大众日报
 【 查看PDF版】
【 查看PDF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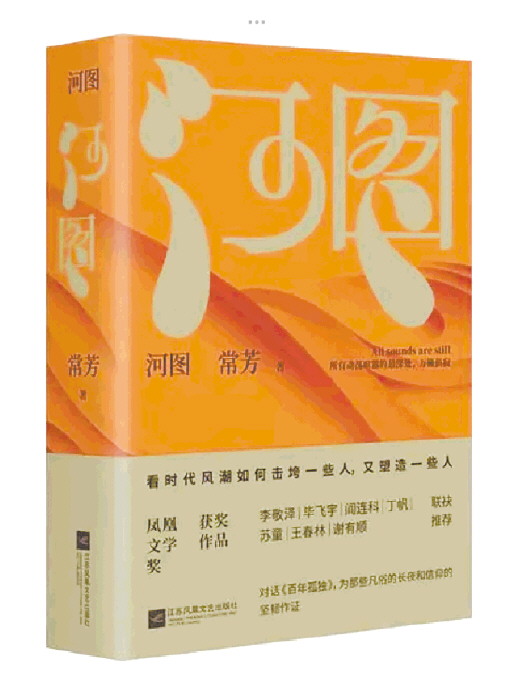 |
|
|
□ 本报记者 刘兰慧
《收获·2022秋卷》发表山东作家常芳的长篇小说《河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于2023年1月出版单行本。小说在故事情节铺陈、历史场景描绘、人物形象塑造、隐秘心理揭示等方面皆明显区别于以往的革命历史叙事,被誉为是一部标记作家本人叙述风格转变和当代文学革命历史叙事方式创新的作品,是一部以人物隐秘内心世界的风云变幻来推动叙事前行的民族心灵秘史。日前,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王西强发起的“云端读书会”,以“《河图》何图?”为主题邀请常芳展开对谈,挖掘《河图》背后的创作故事。
偏方何来?乡土小说家吗?
常芳曾思考“我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作家?”这一问题,这大概可以追溯到她童年时期的那些乡村经验以及中国农耕文明的悠久历史,直到辛亥革命后才与西方舶来的“现代化”一词相连接。她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的中国作家都没有真正摆脱掉身体以及精神上的“乡土”基因。
《河图》中写到不少民间偏方,关于插入偏方的审美意图,常芳表示自己旨在借此象征辛亥革命时期革命者们对时代进步的一种探索。上下求索救国良方的过程里,有些“偏方”也不免会被这些革命者拿来当作“救命”稻草。
与偏方相互映衬的,还有小说里那些童谣。那个名叫周约瑟的车夫,反复在心里吟唱和呼应这些童谣的时候,他可能是在用童年愉悦的心,去覆盖时代巨变所给他带来的巨大撞击。
这些偏方与童谣、神话故事和传说,同小说中的现实生活交织在一起,表达出在轰然到来的辛亥革命这个没有预期的时代背景中,革命者、醋园工人、剃头匠、杂货铺子掌柜、贩夫走卒等泺口的各色人物在面对时代变局时的茫然。
因此,小说便像《鹅笼书生》故事那般,一边是无限的玄幻一边又有无限的可能。
《河图》的句式?童年的记忆?
常芳力图采用一种更加“现代化”的语言,以此来表现西方文明进入中国这一古老的农耕国家之际所形成的撞击。
小说部分地嵌入西班牙语、英语和德语语段,插入西方歌谣,引入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宫廷故事、美国故事和其他世界各地的故事等,旨在表达辛亥革命时期“西方现代化的进入”呈现出的不可阻挡之势。在新旧交替的时刻,古老的中国早已无力关闭那扇正在被推开的大门。
作家多将童年经验视作巨大而珍贵的馈赠。民间故事和说书人的中国传统话本小说,与常芳“比较原始、有生命力”的修辞手法息息相关。常芳的奶奶特别会讲故事,她的爷爷则经常到说书场子里听书。即便不出门,那个说书人响亮的说书声和手里敲响的渔鼓声,也会穿过土墙和屋顶的茅草,“逼迫”着家人去听那些稀奇古怪的故事。常芳想,说书人的说书声真的是把家里的墙壁都用故事浸透了。
常芳童年的生活环境拥有一种“自然色彩与现代性混杂”的特点。济南是中国第一个自主开埠的城市,对整个山东影响很大。此外,常芳的高祖父独自闯荡世界时在临沂一个小镇上以开饭馆为业。饭馆位于从南京到北京的驿路上,既接待过东洋人,也接待过西洋人。
《河图》何图?何来《河图》?
小说中,南家这个家族和马利亚皆无人物原型。书中唯一有原型的人物是谘议局副议长鹿邑德,这个人物源自常芳在创作《第五战区》时到临沂市沂南县采访所听到的故事。
这一人物原型曾从沂南到日本留学,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且娶了位日本太太。回国之后,他动员父亲卖掉家里上千亩土地,自己带着银两到济南参加辛亥革命,支持山东独立。之后,他便杳无音信。后来,他们家族也曾派人到济南去寻找,但未果。
为什么写《河图》?辛亥革命终结了王朝循环往复的历史,当中国与现代化世界迎面相撞时,西方文明已经像疾驰而来的火车那样,轰轰隆隆地把中华大地给震醒了。
小说要表达的主题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如何变成今日之“中国”,书中关于清朝要灭亡的童谣是作家从《推背图》中截取的一段“预言”。《河图》中的人物无法看到自己的结局,亦无法真正理解何为革命。例如,南怀珠尽管起着引领革命潮流的重要作用,但他被作家塑造得有些模糊。即便他身处革命的漩涡,却也无法看清革命之真相。
“河图”也罢,“易经”也好,至今无解。历史乃至现实,从来也都是处于这种朦胧、混沌、模糊但又滚动前行的状态。在大历史之中,《河图》所写的那些小人物、小人物的思想、小人物对于大历史的看法等皆为盲人摸象之一种,好像置身其中但又不明就里。在常芳看来,这既是现象也是本质。
《收获·2022秋卷》发表山东作家常芳的长篇小说《河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于2023年1月出版单行本。小说在故事情节铺陈、历史场景描绘、人物形象塑造、隐秘心理揭示等方面皆明显区别于以往的革命历史叙事,被誉为是一部标记作家本人叙述风格转变和当代文学革命历史叙事方式创新的作品,是一部以人物隐秘内心世界的风云变幻来推动叙事前行的民族心灵秘史。日前,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王西强发起的“云端读书会”,以“《河图》何图?”为主题邀请常芳展开对谈,挖掘《河图》背后的创作故事。
偏方何来?乡土小说家吗?
常芳曾思考“我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作家?”这一问题,这大概可以追溯到她童年时期的那些乡村经验以及中国农耕文明的悠久历史,直到辛亥革命后才与西方舶来的“现代化”一词相连接。她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的中国作家都没有真正摆脱掉身体以及精神上的“乡土”基因。
《河图》中写到不少民间偏方,关于插入偏方的审美意图,常芳表示自己旨在借此象征辛亥革命时期革命者们对时代进步的一种探索。上下求索救国良方的过程里,有些“偏方”也不免会被这些革命者拿来当作“救命”稻草。
与偏方相互映衬的,还有小说里那些童谣。那个名叫周约瑟的车夫,反复在心里吟唱和呼应这些童谣的时候,他可能是在用童年愉悦的心,去覆盖时代巨变所给他带来的巨大撞击。
这些偏方与童谣、神话故事和传说,同小说中的现实生活交织在一起,表达出在轰然到来的辛亥革命这个没有预期的时代背景中,革命者、醋园工人、剃头匠、杂货铺子掌柜、贩夫走卒等泺口的各色人物在面对时代变局时的茫然。
因此,小说便像《鹅笼书生》故事那般,一边是无限的玄幻一边又有无限的可能。
《河图》的句式?童年的记忆?
常芳力图采用一种更加“现代化”的语言,以此来表现西方文明进入中国这一古老的农耕国家之际所形成的撞击。
小说部分地嵌入西班牙语、英语和德语语段,插入西方歌谣,引入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宫廷故事、美国故事和其他世界各地的故事等,旨在表达辛亥革命时期“西方现代化的进入”呈现出的不可阻挡之势。在新旧交替的时刻,古老的中国早已无力关闭那扇正在被推开的大门。
作家多将童年经验视作巨大而珍贵的馈赠。民间故事和说书人的中国传统话本小说,与常芳“比较原始、有生命力”的修辞手法息息相关。常芳的奶奶特别会讲故事,她的爷爷则经常到说书场子里听书。即便不出门,那个说书人响亮的说书声和手里敲响的渔鼓声,也会穿过土墙和屋顶的茅草,“逼迫”着家人去听那些稀奇古怪的故事。常芳想,说书人的说书声真的是把家里的墙壁都用故事浸透了。
常芳童年的生活环境拥有一种“自然色彩与现代性混杂”的特点。济南是中国第一个自主开埠的城市,对整个山东影响很大。此外,常芳的高祖父独自闯荡世界时在临沂一个小镇上以开饭馆为业。饭馆位于从南京到北京的驿路上,既接待过东洋人,也接待过西洋人。
《河图》何图?何来《河图》?
小说中,南家这个家族和马利亚皆无人物原型。书中唯一有原型的人物是谘议局副议长鹿邑德,这个人物源自常芳在创作《第五战区》时到临沂市沂南县采访所听到的故事。
这一人物原型曾从沂南到日本留学,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且娶了位日本太太。回国之后,他动员父亲卖掉家里上千亩土地,自己带着银两到济南参加辛亥革命,支持山东独立。之后,他便杳无音信。后来,他们家族也曾派人到济南去寻找,但未果。
为什么写《河图》?辛亥革命终结了王朝循环往复的历史,当中国与现代化世界迎面相撞时,西方文明已经像疾驰而来的火车那样,轰轰隆隆地把中华大地给震醒了。
小说要表达的主题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如何变成今日之“中国”,书中关于清朝要灭亡的童谣是作家从《推背图》中截取的一段“预言”。《河图》中的人物无法看到自己的结局,亦无法真正理解何为革命。例如,南怀珠尽管起着引领革命潮流的重要作用,但他被作家塑造得有些模糊。即便他身处革命的漩涡,却也无法看清革命之真相。
“河图”也罢,“易经”也好,至今无解。历史乃至现实,从来也都是处于这种朦胧、混沌、模糊但又滚动前行的状态。在大历史之中,《河图》所写的那些小人物、小人物的思想、小人物对于大历史的看法等皆为盲人摸象之一种,好像置身其中但又不明就里。在常芳看来,这既是现象也是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