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药昆仑”疑云
2025-06-22
作者:
来源:
大众日报
 【 查看PDF版】
【 查看PDF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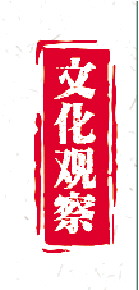 |
|
|
□ 本报记者 周学泽
编者按:
日前,《光明日报》发表《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一文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界和网络上截然分成“两派”观点:一种认为石刻为真,一种认为石刻为伪。“两派”观点互不服气,引发众多关注,为此,记者采访有关专家,力求解疑释惑。
6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仝涛在《光明日报》发表《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一文,解读了青海省玛多县一块古代摩崖石刻题记的内容。
文章中称,青海省玛多县海拔4300米的扎陵湖和鄂陵湖是黄河源区最大的两个淡水湖,近期在扎陵湖北岸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一处37字秦代摩崖石刻题记。该石刻所镌字体为秦小篆,内容为:“皇帝/使五/大夫臣翳/将方士/采藥昆/陯翳以/廿六年三月/己卯車到/此翳□/前□可/一百五十/里。”大意是:秦始皇廿六年,皇帝派遣五大夫翳率领一些方士,乘车前往昆仑山采摘长生不老药。他们于该年三月己卯日到达此地(黄河源头的扎陵湖畔),再前行约一百五十里(到达此行的终点)。
文章认为,该石刻内容及其所在地理位置,解决了国人千古争讼的关于“昆仑”“河源”的精确地望问题。当年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原内地使团之行,也实证了隋唐时期的“唐蕃古道”,在秦始皇时期已经打通了最为关键的环节。文章发布后,众多学者、自媒体人发表了完全相反的意见。
整体风格之辩
上述文章发表后,6月10日,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表示“一眼假”,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制造<昆仑山铭>》说:“高度怀疑乃今人伪刻。”但只有观点,没有论证。6月14日,他又发布《看看真正的秦始皇刻石是什么样》,依然没有文字,但列举了琅琊石刻等图片。
辛德勇着墨不多,但意见很明确,就是从整体风格和形制来讲,青海石刻和秦代皇家刻石差别很大。从琅琊石刻等“秦七刻石”来看,秦代刻石界面确实极为讲究,体现出秦人对铭字立传的严肃性,而青海刻石用小篆刻在粗糙不平、坑坑洼洼的天然石壁上,文字书写的刻意求工与石材处理的粗枝大叶很不相配,仿佛是“到此一游”式的涂鸦。
6月12日,记者采访了山东一位资深石刻研究专家,他表示,就目前提供的图文信息来看,青海“采药昆仑”石刻是否与秦始皇有关,有一些疑点需要排除才能断定,比如,文风问题,一般的秦汉石刻内容,很重视渲染气氛,往往以“兹事体大”的姿态,先从宏大叙事出发,绕一圈再回到本来要说的事,但谈到要说的事,往往说得又不是很具体。著名的“秦七刻石”,基本都是这种风格,比如山东邹城峄山秦代刻石,前半部分刻144字,赞扬秦始皇的正义战争和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给百姓带来的好处,后半部分刻79字记录了李斯随同秦二世出巡时上书请求在秦始皇所立刻石旁刻诏书的情况;青岛黄岛琅琊台遗址的琅琊石刻也是如此,先是说“端平法度,万物之纪”,在“器械一量,同书文字”等国家大事上绕一圈,歌颂秦始皇的圣明和伟大业绩,最后才绕到“乃抚东土,至于琅邪”。
这位经验丰富的专家认为,如果青海“采药昆仑”石刻,是秦始皇派出的采药队伍所刻,是国家行为,皇家所为,依照秦始皇好大喜功的特点,不会草率从事,目前石刻是在一个山岗上,文字叙事简单直露,无铺垫,和一般的秦汉石刻风格不一样,不合常理。
不过,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则认为,“先从文字看,我觉得昆仑刻石的文字时代特征明显,风格统一,看不出什么破绽。”“从文本看,文字简洁,语法规范,‘皇帝+使+人名’‘五大夫+臣+人名’‘将+人名(或职官名、书名)’‘采药+地名’‘以+年月’‘车到此’等简洁准确的表述,与传世秦汉文献中类似的文句对比,毫无违和感。”
也有观点认为,当地环境恶劣,冬季长达半年以上,属典型高寒气候,石刻草率为“到此一游”的记事行为,也不是没有可能。
文字细节之辩
石刻核心问题是内容中的断代问题。西北大学教授曲安京指出,“(皇帝)二十六年三月己卯”与这一年启用的《颛顼历》不符合。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宗迪也发文表示:“《史记》记载秦始皇二十六年灭六国,始议帝号,称皇帝。这块刻石称五大夫(秦始皇)廿六年三月到达河源,元代都实奉命探河源,四月从临夏出发,经4个月方到达河源,以此类推秦人出发,最晚当在始皇二十五年的冬天或者秋天,此时嬴政还没有称皇帝号呢!远在黄河源的五大夫,是如何提前预见到秦始皇称皇帝的?秦代方士早不去晚不去,为何专门挑寒冬天气上路去河源采药?”
来自山东济宁的“求是斋主”6月11日在“求是斋杂谈”公众号撰文指出,这可能是不了解秦代的历法。秦代以十月为岁首,虽然《史记》记载是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的,但据后人考证,其实早在秦昭王时就已经实行以十月为岁首的历法了。所谓以十月为岁首,就是以十月为一年的第一个月,十月初一为一年的第一天。所以,秦王政二十六年,实际上始于上年的十月,二十六年三月已经是当年的第六个月了。注意,只是以十月为岁首,并没有把十月改称为一月或正月,十月还是叫十月,一月还是叫一月或正月(端月)。
故宫博物院器物部金石组副研究馆员熊长云则有另外一说,“由于石刻文字本身的残损漫漶,仝涛识读为‘廿六年’的几个字,并非无可争议。”熊长云认为,“廿六年”或许为“廿七年”,或者为“卅六(或七)年”。“始皇卅七年,三月正有己卯。卅六年,始皇因荧惑守心等事,已预感时日无多。若是卅七年,始皇派使者前往昆仑采药,正合于其时心态。”而且他认为,“铭刻真,不必怀疑。”
刘宗迪还认为,“昆仑采药”一词来自2002年在湖南里耶秦简发现的“琅邪献昆陯五杏药”,并以此质疑,此为当代人见秦简之后去青海伪造石刻。早在2020年7月,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侯光良便已在田野考察中发现这处石刻,此质疑不攻自破。
学者胡文辉从语文学角度提出,石刻中使用的“采药”一词,现在看起来是古代的词汇,但实际上并不见于先秦乃至西汉的文献。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在官方公众号“古文字微刊”撰写文章《我对昆仑刻石的看法》指出:“胡文辉先生说‘采药’一语不见于西汉以前典籍,这没错,‘采药’一语从东汉开始才逐渐增多,但是既然《史记》中有‘采芝药’,不管‘芝’是限定‘药’的,还是与‘药’并列,都说明当时的语言环境中是可以有‘采药’之说的。”
在辩论中,“采药昆仑”石刻文字进一步明确或有别解,比如,有人认为,“方士”应为“方支(技)”,因为“方”下面的残缺字,上面一横是弯曲的,即字不是“士”可以肯定;“行”,一些人认为是“兆”字。还有观点认为,古人“一百”这种表述十分罕见,“一百”一般省略为“百”,这说明“一百五十里”的“一”,有可能是“二或三”。
自然风化之辩
青海“采药昆仑”石刻辨别真伪,最应该辨别的是今天的石刻状态是否符合两千年来的自然风化特征,因为文字书写形式、内容、日期、历法等问题,莫不建于此基础之上。
从石刻文物本体角度来看,针对学者专家提出“此秦代昆仑石刻文字字口与岩石表面石皮色差大,不符合二千多年风吹日晒雨淋风化的特征”,中国科学院大学科技考古专业副教授、石刻研究专家张明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看过“昆仑石刻”高清照片后,综合多年野外考察碑刻经验认为,从字口、包浆以及风化程度来看,该刻石完全符合鉴定界所称的“开门老”特征,“绝无今人仿造的可能”。“仔细观察可见,字口与壁面已自然融为一体,并长覆了一层高原地衣。此外,刻字之后岩面又出现了多次风化断裂,这些裂隙的形成均晚于刻字时间。这些现象都充分说明,字迹形成年代非常古老。”
张明悟表示,关于刻字风化程度,许多人常以想象来推测秦代刻字的状况,然而,若参考全国各地的汉代摩崖石刻以及巴基斯坦洪扎河谷的北魏刻字,会发现很多字迹至今仍非常清晰。
6月12日,山东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任相宏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没到过现场,仅看图片不能辨别真伪,但希望可以考虑借助科学鉴定技术。青海“采药昆仑”石刻如果是真的,那从秦始皇到现在已经2200多年,在如此海拔和气候条件下的长期风化,会在刻痕中形成一些深色的风化物,通过鉴定技术,断定“采药昆仑”石刻的年代,应该不是很困难的事。
此外,秦朝“地不过河西”,秦始皇是否会使人跨过国界采药,也有不少质疑。秦帝国的西界,就是陇西郡西界,没有超出长城一线太远。《史记·大宛列传》明确记载:“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窴,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这表明司马迁写《史记》时,汉人还不知道黄河源出青海,遑论秦始皇时期。当时秦人去河西采药,属于冒险行为。
6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龙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因为没有亲眼看见,对当地的地形地貌以及石刻本身没有太多了解,不敢轻下结论。但坚信这次考古工作者不会造假,其他人造假的目的性也深为可疑,如果石刻真是造假者所为,其水平也相当了得!但是,正如古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所言,其具体细节以及文字反映的历史问题可能还有可商之处。
编者按:
日前,《光明日报》发表《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一文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界和网络上截然分成“两派”观点:一种认为石刻为真,一种认为石刻为伪。“两派”观点互不服气,引发众多关注,为此,记者采访有关专家,力求解疑释惑。
6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仝涛在《光明日报》发表《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一文,解读了青海省玛多县一块古代摩崖石刻题记的内容。
文章中称,青海省玛多县海拔4300米的扎陵湖和鄂陵湖是黄河源区最大的两个淡水湖,近期在扎陵湖北岸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一处37字秦代摩崖石刻题记。该石刻所镌字体为秦小篆,内容为:“皇帝/使五/大夫臣翳/将方士/采藥昆/陯翳以/廿六年三月/己卯車到/此翳□/前□可/一百五十/里。”大意是:秦始皇廿六年,皇帝派遣五大夫翳率领一些方士,乘车前往昆仑山采摘长生不老药。他们于该年三月己卯日到达此地(黄河源头的扎陵湖畔),再前行约一百五十里(到达此行的终点)。
文章认为,该石刻内容及其所在地理位置,解决了国人千古争讼的关于“昆仑”“河源”的精确地望问题。当年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原内地使团之行,也实证了隋唐时期的“唐蕃古道”,在秦始皇时期已经打通了最为关键的环节。文章发布后,众多学者、自媒体人发表了完全相反的意见。
整体风格之辩
上述文章发表后,6月10日,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表示“一眼假”,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制造<昆仑山铭>》说:“高度怀疑乃今人伪刻。”但只有观点,没有论证。6月14日,他又发布《看看真正的秦始皇刻石是什么样》,依然没有文字,但列举了琅琊石刻等图片。
辛德勇着墨不多,但意见很明确,就是从整体风格和形制来讲,青海石刻和秦代皇家刻石差别很大。从琅琊石刻等“秦七刻石”来看,秦代刻石界面确实极为讲究,体现出秦人对铭字立传的严肃性,而青海刻石用小篆刻在粗糙不平、坑坑洼洼的天然石壁上,文字书写的刻意求工与石材处理的粗枝大叶很不相配,仿佛是“到此一游”式的涂鸦。
6月12日,记者采访了山东一位资深石刻研究专家,他表示,就目前提供的图文信息来看,青海“采药昆仑”石刻是否与秦始皇有关,有一些疑点需要排除才能断定,比如,文风问题,一般的秦汉石刻内容,很重视渲染气氛,往往以“兹事体大”的姿态,先从宏大叙事出发,绕一圈再回到本来要说的事,但谈到要说的事,往往说得又不是很具体。著名的“秦七刻石”,基本都是这种风格,比如山东邹城峄山秦代刻石,前半部分刻144字,赞扬秦始皇的正义战争和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给百姓带来的好处,后半部分刻79字记录了李斯随同秦二世出巡时上书请求在秦始皇所立刻石旁刻诏书的情况;青岛黄岛琅琊台遗址的琅琊石刻也是如此,先是说“端平法度,万物之纪”,在“器械一量,同书文字”等国家大事上绕一圈,歌颂秦始皇的圣明和伟大业绩,最后才绕到“乃抚东土,至于琅邪”。
这位经验丰富的专家认为,如果青海“采药昆仑”石刻,是秦始皇派出的采药队伍所刻,是国家行为,皇家所为,依照秦始皇好大喜功的特点,不会草率从事,目前石刻是在一个山岗上,文字叙事简单直露,无铺垫,和一般的秦汉石刻风格不一样,不合常理。
不过,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则认为,“先从文字看,我觉得昆仑刻石的文字时代特征明显,风格统一,看不出什么破绽。”“从文本看,文字简洁,语法规范,‘皇帝+使+人名’‘五大夫+臣+人名’‘将+人名(或职官名、书名)’‘采药+地名’‘以+年月’‘车到此’等简洁准确的表述,与传世秦汉文献中类似的文句对比,毫无违和感。”
也有观点认为,当地环境恶劣,冬季长达半年以上,属典型高寒气候,石刻草率为“到此一游”的记事行为,也不是没有可能。
文字细节之辩
石刻核心问题是内容中的断代问题。西北大学教授曲安京指出,“(皇帝)二十六年三月己卯”与这一年启用的《颛顼历》不符合。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宗迪也发文表示:“《史记》记载秦始皇二十六年灭六国,始议帝号,称皇帝。这块刻石称五大夫(秦始皇)廿六年三月到达河源,元代都实奉命探河源,四月从临夏出发,经4个月方到达河源,以此类推秦人出发,最晚当在始皇二十五年的冬天或者秋天,此时嬴政还没有称皇帝号呢!远在黄河源的五大夫,是如何提前预见到秦始皇称皇帝的?秦代方士早不去晚不去,为何专门挑寒冬天气上路去河源采药?”
来自山东济宁的“求是斋主”6月11日在“求是斋杂谈”公众号撰文指出,这可能是不了解秦代的历法。秦代以十月为岁首,虽然《史记》记载是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的,但据后人考证,其实早在秦昭王时就已经实行以十月为岁首的历法了。所谓以十月为岁首,就是以十月为一年的第一个月,十月初一为一年的第一天。所以,秦王政二十六年,实际上始于上年的十月,二十六年三月已经是当年的第六个月了。注意,只是以十月为岁首,并没有把十月改称为一月或正月,十月还是叫十月,一月还是叫一月或正月(端月)。
故宫博物院器物部金石组副研究馆员熊长云则有另外一说,“由于石刻文字本身的残损漫漶,仝涛识读为‘廿六年’的几个字,并非无可争议。”熊长云认为,“廿六年”或许为“廿七年”,或者为“卅六(或七)年”。“始皇卅七年,三月正有己卯。卅六年,始皇因荧惑守心等事,已预感时日无多。若是卅七年,始皇派使者前往昆仑采药,正合于其时心态。”而且他认为,“铭刻真,不必怀疑。”
刘宗迪还认为,“昆仑采药”一词来自2002年在湖南里耶秦简发现的“琅邪献昆陯五杏药”,并以此质疑,此为当代人见秦简之后去青海伪造石刻。早在2020年7月,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侯光良便已在田野考察中发现这处石刻,此质疑不攻自破。
学者胡文辉从语文学角度提出,石刻中使用的“采药”一词,现在看起来是古代的词汇,但实际上并不见于先秦乃至西汉的文献。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在官方公众号“古文字微刊”撰写文章《我对昆仑刻石的看法》指出:“胡文辉先生说‘采药’一语不见于西汉以前典籍,这没错,‘采药’一语从东汉开始才逐渐增多,但是既然《史记》中有‘采芝药’,不管‘芝’是限定‘药’的,还是与‘药’并列,都说明当时的语言环境中是可以有‘采药’之说的。”
在辩论中,“采药昆仑”石刻文字进一步明确或有别解,比如,有人认为,“方士”应为“方支(技)”,因为“方”下面的残缺字,上面一横是弯曲的,即字不是“士”可以肯定;“行”,一些人认为是“兆”字。还有观点认为,古人“一百”这种表述十分罕见,“一百”一般省略为“百”,这说明“一百五十里”的“一”,有可能是“二或三”。
自然风化之辩
青海“采药昆仑”石刻辨别真伪,最应该辨别的是今天的石刻状态是否符合两千年来的自然风化特征,因为文字书写形式、内容、日期、历法等问题,莫不建于此基础之上。
从石刻文物本体角度来看,针对学者专家提出“此秦代昆仑石刻文字字口与岩石表面石皮色差大,不符合二千多年风吹日晒雨淋风化的特征”,中国科学院大学科技考古专业副教授、石刻研究专家张明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看过“昆仑石刻”高清照片后,综合多年野外考察碑刻经验认为,从字口、包浆以及风化程度来看,该刻石完全符合鉴定界所称的“开门老”特征,“绝无今人仿造的可能”。“仔细观察可见,字口与壁面已自然融为一体,并长覆了一层高原地衣。此外,刻字之后岩面又出现了多次风化断裂,这些裂隙的形成均晚于刻字时间。这些现象都充分说明,字迹形成年代非常古老。”
张明悟表示,关于刻字风化程度,许多人常以想象来推测秦代刻字的状况,然而,若参考全国各地的汉代摩崖石刻以及巴基斯坦洪扎河谷的北魏刻字,会发现很多字迹至今仍非常清晰。
6月12日,山东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任相宏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没到过现场,仅看图片不能辨别真伪,但希望可以考虑借助科学鉴定技术。青海“采药昆仑”石刻如果是真的,那从秦始皇到现在已经2200多年,在如此海拔和气候条件下的长期风化,会在刻痕中形成一些深色的风化物,通过鉴定技术,断定“采药昆仑”石刻的年代,应该不是很困难的事。
此外,秦朝“地不过河西”,秦始皇是否会使人跨过国界采药,也有不少质疑。秦帝国的西界,就是陇西郡西界,没有超出长城一线太远。《史记·大宛列传》明确记载:“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窴,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这表明司马迁写《史记》时,汉人还不知道黄河源出青海,遑论秦始皇时期。当时秦人去河西采药,属于冒险行为。
6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龙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因为没有亲眼看见,对当地的地形地貌以及石刻本身没有太多了解,不敢轻下结论。但坚信这次考古工作者不会造假,其他人造假的目的性也深为可疑,如果石刻真是造假者所为,其水平也相当了得!但是,正如古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所言,其具体细节以及文字反映的历史问题可能还有可商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