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媒体记者到内容创客,他成长与蜕变的背后,暗藏着一代媒体人的迭代进击与转型发展之路——
内容创客于立坤
2024-08-02
作者:
来源:
大众日报
 【 查看PDF版】
【 查看PDF版】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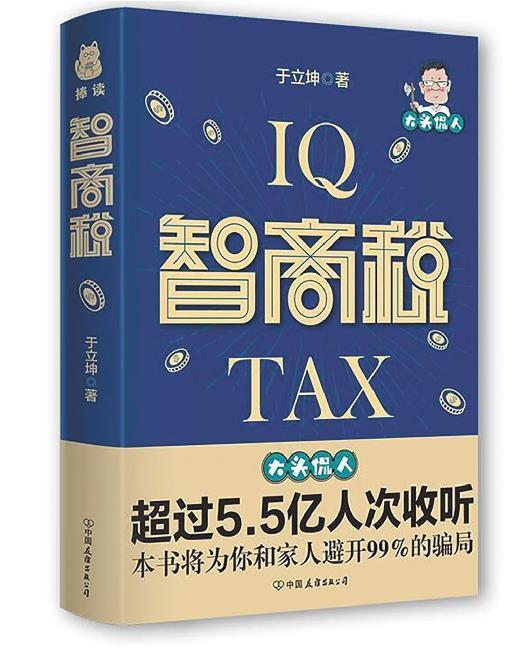 |
|
|
□ 石念军 李雨鑫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你或许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但你或许听过他的节目:《大头侃人》。
追随音频资讯热潮而生的《大头侃人》,自2018年上线以来,单平台播放量累计超过15亿,稳居平台TOP榜单NO.1。对于一名以财经人物传记为核心的严肃内容主播而言,这一成绩殊为难得。
你或许没有见过生活中的他,但你或许早已羡慕过他的生活。由他参与主创的短视频IP《熊起不惑居》,就像是一处“桃花源”,持续向百万粉丝分享向往的生活。
他是资讯平台的达人主播,更是现实世界里砥砺前行的内容创客。从传统媒体时代的电视记者、纸媒从业者,到新媒体时代的音频节目博主、视频栏目主创,他就像是冲锋在流量浪潮中的一骑先锋,在左突右冲之中不断抢滩新陆、抢占新机。
他就是于立坤。曾经共有的媒体人经历,让我对他的采访与观察,充满了对自我职业角色的唤醒、反思、校正与重塑之感:在这个媒介形态与传媒业态高速迭代的时代里,作为媒体人,究竟该如何突破窠臼,应时而变、顺势而为?
显然,从媒体记者到内容创客,他成长与蜕变的背后,实际暗藏着一代媒体人的迭代进击与转型发展之路。
达人主播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适逢第三十二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济召开。于立坤置身其中,乐此不疲。
一方面,读书是他的最大兴趣,也是他平台IP的核心人设标签。如此规模的主题盛会来到家门口,怎么能够错过?何况其内容电商的核心产品类目,恰是图书。
另一方面,出版商一时云集,既要招待老友,又要洽谈新朋,免不了尽地主之谊的应酬与接待。好在他滴酒不沾,可以省去很多麻烦、节约不少时间。他总算能够忙里偷闲,与作家岳南相约直播间,作了一番关于读书与写作的访谈与对话。
在出版商眼里,作为音频平台上首屈一指的达人主播和短视频平台上潜力满满的读书博主,他不仅是优质的带货达人而且是高效的畅销书作家。这都是被验证过的,其《智商税》《任正非传》等著作都曾畅销一时。
于立坤的成名作是音频节目《大头侃人》。这档以当代企业家传记为核心的财经节目,也是他迄今最为重要的代表作。自2018年上线以来,单平台累计播放量已经超过15亿。尤其是近三年来,《大头侃人》以一周两期的低频更新,长期占据平台播放量TOP榜单榜首。
回想《大头侃人》上线之初,于立坤与合伙人鲍良从未奢想过如此情形。乃至当节目首次实现1亿播放量关口之时,两人一遍遍数着1后面长长的0,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在五星级餐厅包下一间宴会厅,广邀亲朋共享破圈的喜悦与骄傲,并信誓旦旦地告诉大家,以后会“庆祝每一个亿”。孰料,节目播放量的累积一亿更比一亿快,二人再也没有大摆筵席的喜悦与冲动,也因此在走红之路上越走越远。
先是平台追身而来。在《大头侃人》节目上线的第二年,一家头部音频资讯平台就找到了于立坤和鲍良,希望能够独家买断《大头侃人》的内容。双方就此开始了长达5年的版权合作,也开启了彼此的互相成就之路。
更有粉丝会聚而来。在一个很偶然的场景,于立坤发现自己有了粉丝。那是2018年的一天,他在医院挂号之际,刚与工作人员开腔对话,身后一位陌生女子突然发问:“你是大头老师吧?”这可把他吓了一大跳,对于互联网的影响力有了直观的体验。现在,《大头侃人》节目的微信粉丝群已达数十个,不得不专门聘用客服维护日常。
也有同行尾随而来。被模仿甚至被剽窃,既让于立坤觉得节目可能真的挺好,又让他和合伙人有苦难言。甚至他们也曾发现,有一个挺火的博主,文案竟然完全抄袭《大头侃人》。二人自嘲这也许就是成名的烦恼吧。
流量时代,谁抢占流量谁就是明星的机会法则,赋予普通人一夕成名的机遇与可能。相比之下,以严肃内容获取流量的于立坤,所获得的成绩颇为难得。更为难得的是,自投身内容创业以来的6年时间里,一路追求流行的他,没有成为“流星”。持续稳定的内容输出能力和对平台规则的洞察,让他和伙伴们看起来就像是冲浪的老手,踩在流量的浪潮之上与时共舞。
内容创客
在我看来,于立坤本质上是一位内容创客。
他毫不讳言自己的商业追求。毕竟,但凡全职投入的工作,就注定不仅仅是职业,而是事实意义上的事业。
以内容产品的生产与传播为手段,积聚影响、会聚用户,进而实现商业价值的变现。从商业逻辑上讲,内容服务业与其他行业是一样的,核心都是以产品达成干预生活的能力,服务社会需求、创造利润空间、实现财富积累。不同之处在于,于立坤的产品路径是以知识分享为核心的内容产品,而非其他。
内容创业,核心是创什么?作为于立坤团队产品思维的极致呈现,通过《大头侃人》和《熊起不惑居》我们可以看到,其核心是以大众的价值需求为导向,持续输出公众应知而未知的正向价值内容,以正向价值的碰撞与共情会聚用户、积聚影响。
产品思维是内容创业的核心。设计、生产与销售,三大环节构成的“微笑曲线”,形成生产型企业的价值闭环。内容生产型企业也一样。
一如市场的共识,产品思维要遵循痛点思维,产品的设计研发要聚焦大众日常生活中的普遍痛点。从这一维度上考量,《大头侃人》的上线,恰暗合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热潮,迎合了社会大众对企业家创业史的认知饥渴。《熊起不惑居》的诞生则适应了人们对田园生活与快意人生的期盼与想象。定位的成功为产品的流行创造了空间与可能。
生产层面,质与量双重稳定的产品输出,则让品牌输出成为一种可能。得益于长期的阅读积累,其貌不扬而头部硕大的于立坤,脑洞硕大。既知识丰厚又言语幽默,一旦开腔,往往滔滔不绝又引人入胜。合伙人鲍良常常听他讲上数小时,而毫不厌倦。于立坤说,《大头侃人》栏目的创设灵感,就来自鲍良最初的鼓动。
不仅有知识储备,而且全情投入。于立坤说,为保障节目的质量和数量,他与合伙人鲍良几乎每周都要在办公室熬几个通宵。常常是他播音时,鲍良睡觉;鲍良剪辑时,则他睡觉。靠着连轴转的熬夜加班,《大头侃人》的更新频次得以保障。
商业变现是产品价值的终极体现。一个产品只有实现了销售转化才能称得上商品,没有销售转化的产品就是实际意义上的库存。于立坤和鲍良一开始就把商业变现作为内容创作与输出的目标,而不惮于谈钱。如果说《大头侃人》单平台播放量超过15亿的数据,说明其传播的影响力,那么不菲的内容版权合作费用,等于直接定义了其商业价值上的成功。
以商业价值为导向,细分产品、打磨产品、流通产品,是于立坤和鲍良的内容创业法则。早在《大头侃人》初登平台TOP榜单之时,关于内容产品的细分与重塑,就已经着手布局了。自2020年开始,基于《大头侃人》的“大头优选”“大头读书会”“大头诗词会”“大头故事会”等细分产品陆续上线,以差异化的内容形式满足用户群体的差异化需求。
其中,“大头优选”定位向粉丝推荐好物,“大头读书会”服务于粉丝的深度阅读需求,“大头诗词会”瞄准用户的亲子阅读时间,“大头故事会”聚焦于历史人物的故事分享。这些细分的垂类栏目都曾实现可观的商业收入,成为业界关注的样本和朋友们引以为傲的榜样。
可以说,如果没有对内容产品的深刻理解和对商业逻辑的严格遵循,就不会有其内容创业的今日之果。于立坤坦言,如果其内容产品没有达成变现,那么,全职投入其中的他们肯定支撑不下去。
诚如业界的共识,不以流量变现为目的的内容生产,终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唯有商业价值的提升与变现,才是对内容生产最好的正向激励。从这一点上说,于立坤他们做到了。
媒体本色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于立坤就职于媒体机构。
2003年大学毕业之后,他的第一份工作是省内一市级电视台的记者岗位。在很多人的记忆里,那是一个新闻理想迸发的黄金时期。《南方周末》《焦点访谈》澎湃着一代人的激情与梦想,都市报和电视民生新闻的普及,让新闻有机会直接表现出干预本地生活的能力与价值,成为市民生活中的必需品之一。
一年零七个月的电视台民生记者经历,让于立坤更加清晰地感觉到新闻的力量。2004年的夏天,机缘巧合之下,他来到了济南,加入了一家媒体机构,继续他的新闻梦。
于立坤自信不是媒体的从业经历,唤醒了他内心的新闻理想,而是根植于心的新闻理想让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媒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年龄的增长,他越发感觉舒适安逸的工作似乎并不能满足自己的人生求索。在年满30岁的2010年,他毅然选择了辞职,北上首都重新寻找人生的可能。
从此一晃就是14年。犹如两个均分的阶段,离开媒体以后的第一个7年,于立坤卖过软件、搞过培训,既做过打工人也曾在创业中感知老板的围城之味。迄今的第二个7年,他与鲍良联合创办《大头侃人》《熊起不惑居》,以自媒体的方式投身内容创业,以不是媒体人胜似媒体人的身份,重返公共舆论场。
因为职业的缘故,访谈期间我总是想到与媒体、记者相关的诸多问题。比如,于立坤的内容产品算不算新闻内容?作为记者的我,与作为内容创作者的于立坤,有哪些同与不同?抛开从业资格认证不谈,机构媒体人和自媒体人的边界在哪里?
于立坤认为自己仍然是一名媒体人,或者说传媒人。因为从商业逻辑上来看,他所做的与机构媒体相比并无二致,都是以优质内容的生产与供给积聚影响力,以影响力的变现为支持,实现更大规模、更为优质的内容生产与供给。但从组织架构和管理形态上看,二者又是截然不同的。机构媒体是庞杂的,是大而全的;其团队则是垂直细分的,是小而美的。
作为曾经的机构媒体从业者,他更清楚现在与过去的不同。那就是作为机构媒体的记者,往往只需要考虑内容的采写与制作这一生产环节,而疏于对创意设计与传播转化的投入与管控。这与机构媒体的组织分工有关,也与媒体内部的绩效考核体系有关。于立坤笑言,他们的自我考核则很直接,如果不能汇聚流量、转化流量,团队就没有营收。不同的考核体系产生不同的激励,彼此工作状态差异明显也就不难理解。
不是媒体,而始终以媒体人的标准要求自己。谈及《大头侃人》的宗旨,于立坤说,创设之初,他和鲍良就确定了三条核心价值原则:传播常识、捍卫理性、传递希望。内容形态则追求“有趣、有料、有用”,着力于公众应知而未知的正向内容传播。
显然,在公共价值的发掘与传播这一维度上,其价值取向与机构媒体是一致的。这是其媒体人底色的呈现,也是其内容创业达成良性循环的基础。
迭代进击
于立坤因《大头侃人》而成名,但其作品并不限于此。
2022年,他与鲍良共同创办抖音短视频栏目《熊起不惑居》,一年之内达成百万粉丝;次年转战视频号,主推文旅内容,三个月涨粉百万。在媒介形态、传媒业态高速迭代、跨越式发展的变局时代,他始终保持着迭代的能力和进击的实践。
综观于立坤的成长经历,可以说,从其入职地方电视台的2003年到如今的21年间,恰是媒介技术快速革新、媒介形态高速迭代、传媒业态剧烈转变的一个时期。而从某种程度上讲,其个人的经历与探索,似乎恰恰顺应了此间传媒业态的变与不变。
变化的是表现形式,不变的是内在逻辑。传媒业态的核心逻辑是舆论影响力的营造和营销。舆论影响力来自哪里?来自用户的关注,以及关注的汇聚与表达。于立坤在地方电视台、行业媒体、蜻蜓FM、抖音、视频号等不同平台之间的辗转腾挪,实际都在追求一种东西,那就是到用户规模更大的地方去、到用户距离最近的地方去、到用户黏性最高的地方去。
“选择不同的平台,其实就是选择不同的流量池。”于立坤说,流量就是一个个的人,人的会聚也就形成了流量池。只有在用户更多、距离更近、黏性更高的流量池里,他们才有机会获得更多的流量,汇聚更多的关注,形成更高的影响力,洞开更大的商业转化空间。“内容创业的根本是让好内容撬动大流量,但绝不是唯流量而论,不能为了迎合流量而失守内容底线。”
他们深知,跟风式一哄而上的流量,来得快消失得更快,并不具有产业转化价值。真正有转化空间的是持续稳定的优质内容供给。
变化的是介质语言,不变的是内容本身。从电视影像语言,到平面纸媒文字,到音频节目生产,到短视频内容创作……在媒介形态日新月异的21年里,于立坤就像是踩着风火轮,应时而变、顺势而为,以不同的内容形态适应着新主流介质的内容需求。他的感受是,流量时代,介质在变、平台在变,唯有内容本身并无太大的改变。因为真正的好内容,不管以任何介质语言呈现,只要符合介质特征就会是好内容。
其合伙人鲍良曾经说过,在做《大头侃人》之前,他根本不懂音频剪辑,完全是被逼着自学成才。可以说,正是得益于其技能包的即时更新与不断丰富,他们始终掌握着最新的介质语言。
变化的是传播形态,不变的是共情本身。转战音频、视频领域之后,与用户的互动变得更加直接与高频。于立坤也从中寻找内容创作的密码,他发现,自己讲的企业家故事之所以能够打动人,不单单是因为自己长期关注那些功败垂成的企业家,熟悉他们的经历、洞悉他们的内心,更是因为自己曾经躬身入局,亲身经历过创业的挫败与不易。在他看来,这就是共情的力量。显然,在传播形态的迭代变化之中,共情的力量始终在强化而非弱化。
专注,更专业;洞察变化,更拥抱变化。技术革新为内容生产插上产业的翅膀,掀起全民内容创业的新浪潮。于立坤坚信,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全媒体,变化的只是介质形态,不变的是需求本身。而内容市场越是泥沙俱下,对优质内容的需求规模就会愈加庞大。内容创业的盛世不是过去也非未来,恰是当下。
从21年前的小城记者到如今的内容创客,于立坤的迭代进击之路,是一个传媒人在变局时代不断完善自我修养的生动实践,更是一代传媒人应时而变顺势而为的时代缩影。
内容产业化之路可以走多远?于立坤的实践证明,在“正能量、大流量”的前提下,只要能够持续稳定地供给符合主流审美调性、满足主流价值需求的优质内容,就有无限可能。也唯有如此,才会有可能。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你或许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但你或许听过他的节目:《大头侃人》。
追随音频资讯热潮而生的《大头侃人》,自2018年上线以来,单平台播放量累计超过15亿,稳居平台TOP榜单NO.1。对于一名以财经人物传记为核心的严肃内容主播而言,这一成绩殊为难得。
你或许没有见过生活中的他,但你或许早已羡慕过他的生活。由他参与主创的短视频IP《熊起不惑居》,就像是一处“桃花源”,持续向百万粉丝分享向往的生活。
他是资讯平台的达人主播,更是现实世界里砥砺前行的内容创客。从传统媒体时代的电视记者、纸媒从业者,到新媒体时代的音频节目博主、视频栏目主创,他就像是冲锋在流量浪潮中的一骑先锋,在左突右冲之中不断抢滩新陆、抢占新机。
他就是于立坤。曾经共有的媒体人经历,让我对他的采访与观察,充满了对自我职业角色的唤醒、反思、校正与重塑之感:在这个媒介形态与传媒业态高速迭代的时代里,作为媒体人,究竟该如何突破窠臼,应时而变、顺势而为?
显然,从媒体记者到内容创客,他成长与蜕变的背后,实际暗藏着一代媒体人的迭代进击与转型发展之路。
达人主播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适逢第三十二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济召开。于立坤置身其中,乐此不疲。
一方面,读书是他的最大兴趣,也是他平台IP的核心人设标签。如此规模的主题盛会来到家门口,怎么能够错过?何况其内容电商的核心产品类目,恰是图书。
另一方面,出版商一时云集,既要招待老友,又要洽谈新朋,免不了尽地主之谊的应酬与接待。好在他滴酒不沾,可以省去很多麻烦、节约不少时间。他总算能够忙里偷闲,与作家岳南相约直播间,作了一番关于读书与写作的访谈与对话。
在出版商眼里,作为音频平台上首屈一指的达人主播和短视频平台上潜力满满的读书博主,他不仅是优质的带货达人而且是高效的畅销书作家。这都是被验证过的,其《智商税》《任正非传》等著作都曾畅销一时。
于立坤的成名作是音频节目《大头侃人》。这档以当代企业家传记为核心的财经节目,也是他迄今最为重要的代表作。自2018年上线以来,单平台累计播放量已经超过15亿。尤其是近三年来,《大头侃人》以一周两期的低频更新,长期占据平台播放量TOP榜单榜首。
回想《大头侃人》上线之初,于立坤与合伙人鲍良从未奢想过如此情形。乃至当节目首次实现1亿播放量关口之时,两人一遍遍数着1后面长长的0,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在五星级餐厅包下一间宴会厅,广邀亲朋共享破圈的喜悦与骄傲,并信誓旦旦地告诉大家,以后会“庆祝每一个亿”。孰料,节目播放量的累积一亿更比一亿快,二人再也没有大摆筵席的喜悦与冲动,也因此在走红之路上越走越远。
先是平台追身而来。在《大头侃人》节目上线的第二年,一家头部音频资讯平台就找到了于立坤和鲍良,希望能够独家买断《大头侃人》的内容。双方就此开始了长达5年的版权合作,也开启了彼此的互相成就之路。
更有粉丝会聚而来。在一个很偶然的场景,于立坤发现自己有了粉丝。那是2018年的一天,他在医院挂号之际,刚与工作人员开腔对话,身后一位陌生女子突然发问:“你是大头老师吧?”这可把他吓了一大跳,对于互联网的影响力有了直观的体验。现在,《大头侃人》节目的微信粉丝群已达数十个,不得不专门聘用客服维护日常。
也有同行尾随而来。被模仿甚至被剽窃,既让于立坤觉得节目可能真的挺好,又让他和合伙人有苦难言。甚至他们也曾发现,有一个挺火的博主,文案竟然完全抄袭《大头侃人》。二人自嘲这也许就是成名的烦恼吧。
流量时代,谁抢占流量谁就是明星的机会法则,赋予普通人一夕成名的机遇与可能。相比之下,以严肃内容获取流量的于立坤,所获得的成绩颇为难得。更为难得的是,自投身内容创业以来的6年时间里,一路追求流行的他,没有成为“流星”。持续稳定的内容输出能力和对平台规则的洞察,让他和伙伴们看起来就像是冲浪的老手,踩在流量的浪潮之上与时共舞。
内容创客
在我看来,于立坤本质上是一位内容创客。
他毫不讳言自己的商业追求。毕竟,但凡全职投入的工作,就注定不仅仅是职业,而是事实意义上的事业。
以内容产品的生产与传播为手段,积聚影响、会聚用户,进而实现商业价值的变现。从商业逻辑上讲,内容服务业与其他行业是一样的,核心都是以产品达成干预生活的能力,服务社会需求、创造利润空间、实现财富积累。不同之处在于,于立坤的产品路径是以知识分享为核心的内容产品,而非其他。
内容创业,核心是创什么?作为于立坤团队产品思维的极致呈现,通过《大头侃人》和《熊起不惑居》我们可以看到,其核心是以大众的价值需求为导向,持续输出公众应知而未知的正向价值内容,以正向价值的碰撞与共情会聚用户、积聚影响。
产品思维是内容创业的核心。设计、生产与销售,三大环节构成的“微笑曲线”,形成生产型企业的价值闭环。内容生产型企业也一样。
一如市场的共识,产品思维要遵循痛点思维,产品的设计研发要聚焦大众日常生活中的普遍痛点。从这一维度上考量,《大头侃人》的上线,恰暗合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热潮,迎合了社会大众对企业家创业史的认知饥渴。《熊起不惑居》的诞生则适应了人们对田园生活与快意人生的期盼与想象。定位的成功为产品的流行创造了空间与可能。
生产层面,质与量双重稳定的产品输出,则让品牌输出成为一种可能。得益于长期的阅读积累,其貌不扬而头部硕大的于立坤,脑洞硕大。既知识丰厚又言语幽默,一旦开腔,往往滔滔不绝又引人入胜。合伙人鲍良常常听他讲上数小时,而毫不厌倦。于立坤说,《大头侃人》栏目的创设灵感,就来自鲍良最初的鼓动。
不仅有知识储备,而且全情投入。于立坤说,为保障节目的质量和数量,他与合伙人鲍良几乎每周都要在办公室熬几个通宵。常常是他播音时,鲍良睡觉;鲍良剪辑时,则他睡觉。靠着连轴转的熬夜加班,《大头侃人》的更新频次得以保障。
商业变现是产品价值的终极体现。一个产品只有实现了销售转化才能称得上商品,没有销售转化的产品就是实际意义上的库存。于立坤和鲍良一开始就把商业变现作为内容创作与输出的目标,而不惮于谈钱。如果说《大头侃人》单平台播放量超过15亿的数据,说明其传播的影响力,那么不菲的内容版权合作费用,等于直接定义了其商业价值上的成功。
以商业价值为导向,细分产品、打磨产品、流通产品,是于立坤和鲍良的内容创业法则。早在《大头侃人》初登平台TOP榜单之时,关于内容产品的细分与重塑,就已经着手布局了。自2020年开始,基于《大头侃人》的“大头优选”“大头读书会”“大头诗词会”“大头故事会”等细分产品陆续上线,以差异化的内容形式满足用户群体的差异化需求。
其中,“大头优选”定位向粉丝推荐好物,“大头读书会”服务于粉丝的深度阅读需求,“大头诗词会”瞄准用户的亲子阅读时间,“大头故事会”聚焦于历史人物的故事分享。这些细分的垂类栏目都曾实现可观的商业收入,成为业界关注的样本和朋友们引以为傲的榜样。
可以说,如果没有对内容产品的深刻理解和对商业逻辑的严格遵循,就不会有其内容创业的今日之果。于立坤坦言,如果其内容产品没有达成变现,那么,全职投入其中的他们肯定支撑不下去。
诚如业界的共识,不以流量变现为目的的内容生产,终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唯有商业价值的提升与变现,才是对内容生产最好的正向激励。从这一点上说,于立坤他们做到了。
媒体本色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于立坤就职于媒体机构。
2003年大学毕业之后,他的第一份工作是省内一市级电视台的记者岗位。在很多人的记忆里,那是一个新闻理想迸发的黄金时期。《南方周末》《焦点访谈》澎湃着一代人的激情与梦想,都市报和电视民生新闻的普及,让新闻有机会直接表现出干预本地生活的能力与价值,成为市民生活中的必需品之一。
一年零七个月的电视台民生记者经历,让于立坤更加清晰地感觉到新闻的力量。2004年的夏天,机缘巧合之下,他来到了济南,加入了一家媒体机构,继续他的新闻梦。
于立坤自信不是媒体的从业经历,唤醒了他内心的新闻理想,而是根植于心的新闻理想让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媒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年龄的增长,他越发感觉舒适安逸的工作似乎并不能满足自己的人生求索。在年满30岁的2010年,他毅然选择了辞职,北上首都重新寻找人生的可能。
从此一晃就是14年。犹如两个均分的阶段,离开媒体以后的第一个7年,于立坤卖过软件、搞过培训,既做过打工人也曾在创业中感知老板的围城之味。迄今的第二个7年,他与鲍良联合创办《大头侃人》《熊起不惑居》,以自媒体的方式投身内容创业,以不是媒体人胜似媒体人的身份,重返公共舆论场。
因为职业的缘故,访谈期间我总是想到与媒体、记者相关的诸多问题。比如,于立坤的内容产品算不算新闻内容?作为记者的我,与作为内容创作者的于立坤,有哪些同与不同?抛开从业资格认证不谈,机构媒体人和自媒体人的边界在哪里?
于立坤认为自己仍然是一名媒体人,或者说传媒人。因为从商业逻辑上来看,他所做的与机构媒体相比并无二致,都是以优质内容的生产与供给积聚影响力,以影响力的变现为支持,实现更大规模、更为优质的内容生产与供给。但从组织架构和管理形态上看,二者又是截然不同的。机构媒体是庞杂的,是大而全的;其团队则是垂直细分的,是小而美的。
作为曾经的机构媒体从业者,他更清楚现在与过去的不同。那就是作为机构媒体的记者,往往只需要考虑内容的采写与制作这一生产环节,而疏于对创意设计与传播转化的投入与管控。这与机构媒体的组织分工有关,也与媒体内部的绩效考核体系有关。于立坤笑言,他们的自我考核则很直接,如果不能汇聚流量、转化流量,团队就没有营收。不同的考核体系产生不同的激励,彼此工作状态差异明显也就不难理解。
不是媒体,而始终以媒体人的标准要求自己。谈及《大头侃人》的宗旨,于立坤说,创设之初,他和鲍良就确定了三条核心价值原则:传播常识、捍卫理性、传递希望。内容形态则追求“有趣、有料、有用”,着力于公众应知而未知的正向内容传播。
显然,在公共价值的发掘与传播这一维度上,其价值取向与机构媒体是一致的。这是其媒体人底色的呈现,也是其内容创业达成良性循环的基础。
迭代进击
于立坤因《大头侃人》而成名,但其作品并不限于此。
2022年,他与鲍良共同创办抖音短视频栏目《熊起不惑居》,一年之内达成百万粉丝;次年转战视频号,主推文旅内容,三个月涨粉百万。在媒介形态、传媒业态高速迭代、跨越式发展的变局时代,他始终保持着迭代的能力和进击的实践。
综观于立坤的成长经历,可以说,从其入职地方电视台的2003年到如今的21年间,恰是媒介技术快速革新、媒介形态高速迭代、传媒业态剧烈转变的一个时期。而从某种程度上讲,其个人的经历与探索,似乎恰恰顺应了此间传媒业态的变与不变。
变化的是表现形式,不变的是内在逻辑。传媒业态的核心逻辑是舆论影响力的营造和营销。舆论影响力来自哪里?来自用户的关注,以及关注的汇聚与表达。于立坤在地方电视台、行业媒体、蜻蜓FM、抖音、视频号等不同平台之间的辗转腾挪,实际都在追求一种东西,那就是到用户规模更大的地方去、到用户距离最近的地方去、到用户黏性最高的地方去。
“选择不同的平台,其实就是选择不同的流量池。”于立坤说,流量就是一个个的人,人的会聚也就形成了流量池。只有在用户更多、距离更近、黏性更高的流量池里,他们才有机会获得更多的流量,汇聚更多的关注,形成更高的影响力,洞开更大的商业转化空间。“内容创业的根本是让好内容撬动大流量,但绝不是唯流量而论,不能为了迎合流量而失守内容底线。”
他们深知,跟风式一哄而上的流量,来得快消失得更快,并不具有产业转化价值。真正有转化空间的是持续稳定的优质内容供给。
变化的是介质语言,不变的是内容本身。从电视影像语言,到平面纸媒文字,到音频节目生产,到短视频内容创作……在媒介形态日新月异的21年里,于立坤就像是踩着风火轮,应时而变、顺势而为,以不同的内容形态适应着新主流介质的内容需求。他的感受是,流量时代,介质在变、平台在变,唯有内容本身并无太大的改变。因为真正的好内容,不管以任何介质语言呈现,只要符合介质特征就会是好内容。
其合伙人鲍良曾经说过,在做《大头侃人》之前,他根本不懂音频剪辑,完全是被逼着自学成才。可以说,正是得益于其技能包的即时更新与不断丰富,他们始终掌握着最新的介质语言。
变化的是传播形态,不变的是共情本身。转战音频、视频领域之后,与用户的互动变得更加直接与高频。于立坤也从中寻找内容创作的密码,他发现,自己讲的企业家故事之所以能够打动人,不单单是因为自己长期关注那些功败垂成的企业家,熟悉他们的经历、洞悉他们的内心,更是因为自己曾经躬身入局,亲身经历过创业的挫败与不易。在他看来,这就是共情的力量。显然,在传播形态的迭代变化之中,共情的力量始终在强化而非弱化。
专注,更专业;洞察变化,更拥抱变化。技术革新为内容生产插上产业的翅膀,掀起全民内容创业的新浪潮。于立坤坚信,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全媒体,变化的只是介质形态,不变的是需求本身。而内容市场越是泥沙俱下,对优质内容的需求规模就会愈加庞大。内容创业的盛世不是过去也非未来,恰是当下。
从21年前的小城记者到如今的内容创客,于立坤的迭代进击之路,是一个传媒人在变局时代不断完善自我修养的生动实践,更是一代传媒人应时而变顺势而为的时代缩影。
内容产业化之路可以走多远?于立坤的实践证明,在“正能量、大流量”的前提下,只要能够持续稳定地供给符合主流审美调性、满足主流价值需求的优质内容,就有无限可能。也唯有如此,才会有可能。
